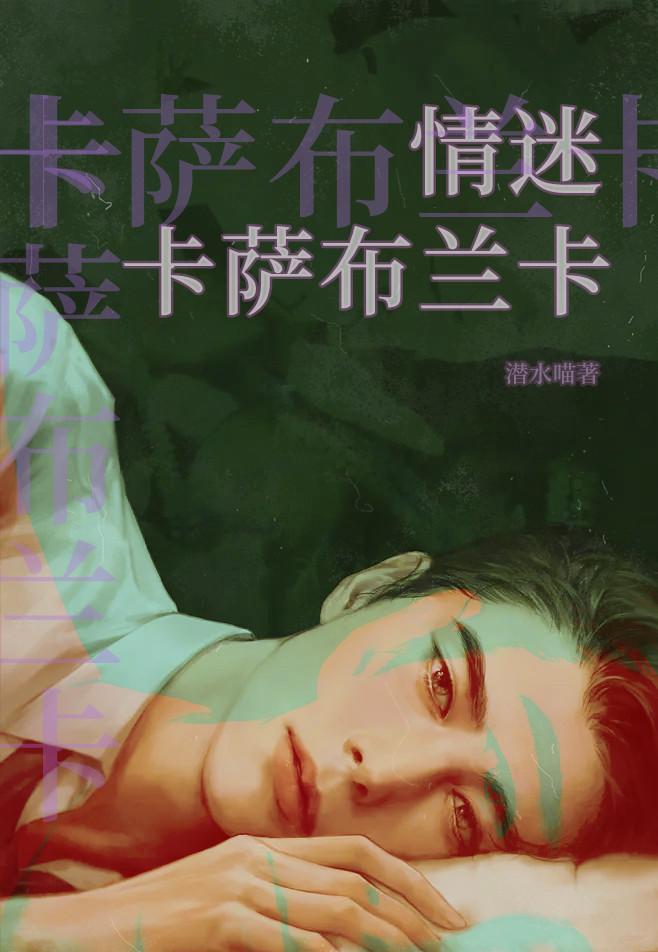91言情>病美人靠刷愧疚值极限求生[快穿] > 120130(第12页)
120130(第12页)
他脑子里反复琢磨的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一个也舍不得在她身上用。
她刚才说情侣纹身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快跳起来了。
挑纹身花纹那会儿,他压根没想那么多,只听说泰国一个纹身师的个人风格,和他要的效果相似,就直接远程找上门去了,还设计下套,让她以为泰国是她自己选的。
不然怕她知道了不肯来。
那纹身师跟他沟通好了图案和细节,还有想要的效果后,顺口问了句他是不是自己纹,他脱口而出是给自己家保姆纹,这句话一说出去,感觉翻译和对面纹身师都默了默。
他自己回头想了想,没想出个名堂来,还是翻译委婉地问他,对方是否知情同意。
他从小没被妥善引导过的脑子里,这才被灌输进了一个新鲜思想——
他对别人的身体没有支配权。
他简单粗暴地决定:
那就自己陪她一起纹。
一个人做会害怕抗拒的事情,两个人做会好很多。
这也是辜苏来到他身边后,慢慢教会他的东西。
他想学以致用,想补偿她,想给她打上标记。
很自私,就连自私这个定义也是他活了二十多年才后知后觉发现的。
可是——他想——这世上真的有丝毫不存私心的人吗?
那他倒想见见,当面问问,如果对方是他,面对辜苏,他妈的是怎么做到坦坦荡荡,清清白白的。
……
纹身师的技术很好,下手利落干净,先给辜苏纹,她纹好之后,就抱着胳膊坐在一边发呆,眼睛是看向沈悯的方向,眼神却没有焦距。
沈悯闭着眼让纹身师在自己脖子上动针,其实是疼的,但辜苏刚才做的时候一声都没吭。
她也太能忍痛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很多苦。
这个念头只在沈悯心里停留了一瞬。
因为答案是肯定的。
就比如他,他能忍痛,是因为就在此时此刻,他正经受着比纹身更痛的,病痛的折磨。
他们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境遇。
痛着痛着,沈悯忽然笑了,他看向辜苏,在她逐渐回神诧异的视线里,伸出手去:
“把手给我。”
辜苏脱了人字拖,把脚提起来缩在一边的单人沙发上,整个人团成一团,不太想动,对他的邀请也爱答不理的。
可能是真的疼,后劲还在。
沈悯固执地抬手,换了种说法:
“手给你。牵一下行不行?”
辜苏莫名其妙看了他一眼,最终还是爬下沙发,走过来牵住他:
“很疼吗?”
“你不是知道?”
他笑的时候面目有些扭曲。
辜苏不说话了,虚虚地牵着他,在他身边站着,站了一会儿累了,就去把沙发拖过来坐着。
等沈悯做完的时候,辜苏已经趴在沙发扶手上睡着了,手指早就没了力气,是沈悯反客为主,捏住了她的手,握在手里。
他很喜欢触碰她,碰哪里都可以。
手很喜欢,腰更喜欢。
他和她都默契地没有把二人之间的关系摆在明面上说,充其量,她算是他的“前保姆”,他是她的“前雇主”。
如今还搅合在一起,全靠他死皮赖脸不放手。
沈悯总觉得,有些事情,一旦说破了,他就真跟那些觊觎她的混蛋——跟沈琢,沈恒,贺连嶂,甚至是那些看她漂亮,大街上就敢过来要联系方式的男的一样了。
他对她的感情,不是想让她做他女朋友的那种,也不是贪恋肉。体的那种。
沈悯在纹身的余痛中想,如今他对她,就像是在暗无天日的洞穴里,已经半盲的夜行生物,守着一株会发出荧光的花。
他不会想去攀折她,不会想去玷污她,只
想守着,静静地守着,不让任何人靠近。
只要被她的光芒惠及,他的眼睛总有一天会重新看到完整的光亮,他的世界也一定会夜尽天明。
沈悯弯下腰,极近地注视着她的睡颜,碰了碰她的脸,又看向她颈侧的纹身。
半个巴掌大小,图案和色彩都很低调,不至于喧宾夺主,图案顺着她形状美好的颈部曲线延展。
他没告诉她,这个图案里其实框了他名字的艺术字,专门请大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