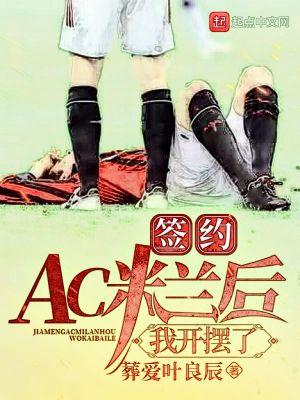91言情>[网王]拂晓的空与蓝色旷道 > 第211章 HE番外5前篇(第2页)
第211章 HE番外5前篇(第2页)
她先是摇了摇头,随後对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说到川岛桑,我认为你应该去找她,她跟教授应该是很长时间了的。”那帧画面又闪过,她的眼睛很疼。
说是她本人的误解也行,但就在逃离现场之後上班的那天,如果不是川岛叫她进去说什麽设备的问题,她应该连个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吧。雨宫觉得自己并不是想要感谢她,可她觉得川岛很可怜,因为或许如果不是在这家公司,不是在这个环境,川岛应该会笑得很灿烂。
为什麽要在说完嘲讽她的话语之後,为她撇下一眼像是生病了的神情,迷途的瞳仁里有过疯狂,然後转身还是继续着已经荒唐的滑稽,那双眼睛就像在对着她说,救救我吧,我是破败不堪的魂魄,我是快要老去的牵牛花,这样的我,脱离墙体,还能等到下一个春天吗?
拐角处转身的力气随着沉下去的天色并肩散了,飘落在空中的那时只有她鼻腔里的水汽,眉眼间萧索的疮痍不是一个人所拥有,雨宫不想已阅,因为嗤笑声声斑驳,回忆里打滚就溶解成了淌血的声音。
可是她知道,如果她这麽说出口,只会显得自己在袒护着谁,可她也想过,觉得想得清楚,她们虽然名字不同,长相不同,但她们无一例外都不过是待宰的羔羊。有的地方将庸俗化为必须坚守的制度,假意厚待你,其实羊毛不过是最终出于羊的肩头。
如果这件事只是弱者们相互拔刀,那以後还会继续産生更多的羔羊,能够完全纯粹,完全能站着要饭吃的人在这世界少之又少,没有队友的时候,他根本就无法祈求多少。
在从前的日子里,八岁之後的时间里,雨宫一直觉得能说这个词就像犯罪,它是一种妄语,又或者说像是一种亡语。如何才能巧妙地过这样那样的日子?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盘旋在心头,对世界的惊奇会不会变成一种束缚,变成一种技巧。
“或许,能否说服她转成像是作为污点证人那样的存在,就是关键吧。让她明白无论背叛自己到什麽程度,其实都拿不到一个能满意的结局,这样对你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才能够成为有利的证据。”
“其实吉冈桑…你也明白不是吗?有些东西…已经失去过一次了。”你已经失去过一次自己说过爱的那个人了,你爱的是那个洁白的娃娃,还是这个人,或许这种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的眼睛已经诉说了这一切。
雨宫的心里明白,让创造问题的人去解决问题,那麽它只会消失,不会被解决。所以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必须要明确的,怒火要对准那个站在金字塔头的那些人的,若能解决完这些,被栖身压在覆雪之下的,不管是漾然的春,还是已经糅杂得不成样的骆驼,才会真的有所谓的出路可言。
语言啊,很多时候都是那样无法自由,她孤身一人没有任何胜算,面对不适皆无能为力,但或许通往奇迹的路上,点亮盏尾灯,曾经她唾弃的技巧去为最後真正的美丽诗篇辗转,每种矛盾都屹立在她的喉咙,她看得见,所以现在想要看得更远。
——去擒贼先擒王吧,即便少女已经听出他依旧手扣着对女朋友的枷锁,但他今天能来找自己,必定是已经想要将所剩不多的一切都豁出去了不是吗。
她曾经拒绝了深入万丈的海沟,但也拒绝了和或许是先锋的人并肩作战的力气,她现在不是一个人,她的身边站着重要的人,既然她也会在心里退缩,那她也认为自己无法成为那个点破对方的小心思的人。
所以曾经她依靠过的,又鄙夷过的语言,第一次让她庆幸她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辗转。
“我会与自己和解的吧?”少女只是扪心自问。祈祷吧,起舞吧,不那麽所谓正义或光彩的绽放也没关系,请去成就那个真正的目标吧,吉冈,然後想要自我赎罪,那就赎,曾经同为奴仆的生活的人,她不会说一句,因为那双流泪的眼睛早已卖出懊悔的一切。
直至吉冈的身影离开,门扉紧闭,幸村还有些沉浸在刚才语出惊人的雨宫的画面里。
“精市…”紧绷的弦断开之後,雨宫泄气地钻进了他的怀抱。
“美泉可以告诉我,为什麽刚才要那麽说嘛?”他轻轻揉着她的头发,从指尖处还能传递上来些许颤抖。
“总觉得,很累了…看到自相残杀的场景,永远只有上头的人在获利。这麽做大扫除得到的或许都是治标不治本,”而痛苦会延续,就像一台轰鸣而过的火车,永远都在没日没夜地叫喊着,永远不停止,“其实我并不完全相信,吉冈是为了女朋友而做这件事,但我也好像说不出什麽谴责的话…”
“会动手打女人的男人为什麽不谴责?”他的表情越发严肃。
“刚才说的话会激怒他的吧?我不想你在我身边一会受到什麽伤害,”雨宫默默叹了口气,“我觉得他还没有看清自己真正的对手在哪里,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对手吧…不管他对我们说得有多义正言辞,他也变相承认了自己是压死女友的最後一根稻草的感觉。总之,我的感觉很复杂,但我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
活着才会有希望,如果连生命都失去了,就不会再有机会碰到所谓的转机了,她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只要是腐烂不堪就得滚蛋,没人能决定谁必须活着,必须拉倒。那个女生应该很需要这份工作吧,但是最後的结局却是自我了结的模样,失业的父母怎麽办都暂且不说了,吉冈不就像是原先想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随後在某个平凡的一天里也被席卷麽。
在这片泥潭里,站往道德高处已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丧钟从来不是为谁而敲,他们这些喽啰其实就是个整体,当听到它响起,无需犹豫,那就是为她们每个人而奏响的,不管是a君接受,还是b君拒绝,两个选项到最後都是一条归路,毫无分别。
“看不清前路的小羔羊们,最终只能去抓住那些看似是最优解的东西,随後顺着那条光明大道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吃着杂草,”她的声音带上了哽咽,眼睛在努力看向窗外照进的阳光,好刺眼啊,可是她想让它再猛烈些,让她一次性流完眼泪,“我很难过,站在分叉路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难过,或许这份难过是因为身在体系里的曾经的我和其他人都没什麽不同,我们都是…奴才。”
“所以你想劝他把刀口不是对准川岛,而是教授,或者说是更中心的人。”
大概,是的吧,所以少女点了点头。
她曾经天真的以为,当一个男人成为了父亲,就会在身份转变的那个瞬间对比自己小的女孩産生想要呵护的心情,就算再平凡,再普通,再向後退一步,这些人应该也不能産生宛如要对自己儿女般的人上手摸索。
是啊,甚至,她只能用儿女,因为吉冈的话说的都是真的,并且讽刺的是她连怀疑都没有。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小…就算他真的捅破了以川岛为主的交易,那只会是川岛被推出来,之後进去的人一样会成为下一个他和她,这样的事情只会反复发生。而且还有一件事,既然川岛能呆在实验室那麽久,我不觉得以她的智商…会什麽证据都没有,打仗也需要战术准备,如果这块石头是不是朝水面精准抛出去的话,它根本翻不起更多的水花。”
“而且川岛如果真能被他说服的话,最後自己也会进去的,”幸村干脆把她没说的话补完,“美泉…真是个很在乎结果的人呢。可是你的心,太软了。”从你阐述的话里,我已经感觉到那份难过。
她没有马上接话,只是靠着他,当年如果她多发呆几秒钟,或许现在她就不是坐在这里,整个世界都会发生变化。生活啊,她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叫鹫宫的老板,朋友,她不能因为自己脱离了火山喷发,就不去感受黑暗里脆弱的跳动。
她能想象得到吉冈前女友到底是什麽心情,她们都不明白为什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越是刹那间本能的思考却是最容易压垮她们这类人,不管是思考为什麽要发生在自己身上,随後感到羞耻,还是思考为什麽自己要感到羞耻,总之,那是个艰难的过程,更何况少女是侥幸逃离掉的那一个,所以那位女孩呢?还有,最後接受了的川岛呢?
雨宫是相信的,相信没有谁如果能有选择会自愿答应那样的事。况且那还是牺牲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东西。
所以时隔多年,她的心哐当地就裂了,就在此刻。
“谢谢你,美泉。”从背後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回响,雨宫有些茫然,慢慢擡头看向他。
“为什麽突然…?”话题跳跃的有些快,她没理清幸村的想法。
“呵呵,没什麽,就是忽然想说谢谢了,”谢谢让他想起那个在网球部的围栏前,一脸正经地长篇大论地说着为他着想添光的话的女孩,谢谢让他能一直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以至于连等待都漫长,“美泉做了很多想让我感谢的事情,所以,就想一直说下去。”
因为她是一个在乎结果的人,所以就连当时幸村去集训的时候设想过的吵架什麽的都从未发生,见不到面的日子里,只要是个有感情的正常人都会忍不住有些小情绪上头吧,可她就像被长谷川刺到的那次一样,连吱一声都没有。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目标,坚持很累,他们都是人,脚都在走在陆地上,所以将心比心,虽然在她的上班日里他会忍不住发点粘人的短信,但绝对不会劝她放下工作。终于现在一切还不算晚,所以往後馀生,都尽情在他的眼中,怀抱里自由地撒娇吧,依靠他,无论什麽时候。
包厢是寂静的,雨宫从未觉得世界如此安静,但幸村从背後搂住自己的温暖让一切都变得祥和。那颗混沌的心被忽然释放了感情,不被觉得奇怪,言不由衷,她已经很高兴。
“什麽嘛…”傲娇那肯定是偶尔还改不了的了,不过…“我也谢谢你,精市,很多很多事情都是。”
“那,我们亲爱的感谢二人组,现在可以准备回家了吗?”
“嗯,走吧,我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