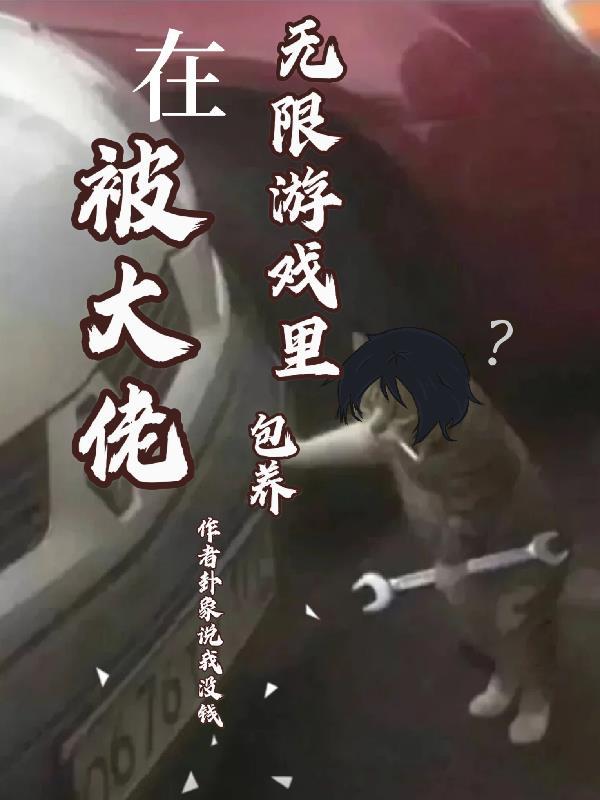91言情>少女前线:141指挥官 > 第1243章 投资(第1页)
第1243章 投资(第1页)
账房把“私生”改写成“旁系投资”,试图用金钱和权势来掩盖那肮脏的本质。
年轻的情妇被安置在阿尔诺河对岸的粉色小楼,楼名学舌鸟,实则暗号待宰,就像一只被关在华丽笼子里的金丝雀,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每逢主家有宴会,她就得穿上最高级的威尼斯锦缎,怀抱婴孩,像展示一件会喘气的抵押品,在众人面前强颜欢笑,却不知背后隐藏着多少阴谋与算计。
然而,真正的抵押品其实是主家自己,他们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早已失去了自我,成为了欲望的奴隶。
在某一年某某个王国内部的某个地方的冬夜,原配夫人的哥哥——那位在罗马教廷挂了号的枢机——派人送来一封短笺,上面只有一行冷冰冰的字:“若不想在复活节讲道时被公开绝罚,就亲自处理干净。”这短短一行字,如同一把锋利的匕,直直地刺进了主家的心脏。
于是,宴会散场后,主人端着温热的葡萄酒走上小楼,酒里浮着几粒苍白的杏仁,那杏仁就像隐藏在甜蜜中的毒药,随时可能夺走情妇的生命。
情妇喝完,把孩子放进摇篮,理了理鬓,像是要赴一场迟到的舞会,脸上还带着一丝虚假的微笑。
药性作前,她最后一次望向窗外:阿尔诺河上浮着碎冰,月光把冰块照成一枚枚未兑现的银币,仿佛在诉说着她那未完成的梦想和破碎的人生。第二天,仆人现她伏在摇篮边,唇角挂着白沫,像雪,又像未说出口的诅咒,那诅咒仿佛是对这个不公世界的控诉。
再往北,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账簿换成了股票,金钱的游戏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用“私生”做杠杆,把私生子包装成“海外总督候选人”,试图用权势和地位来掩盖他们那见不得人的身世。
船只出海前,总督府已备好镶金的婴儿房,那婴儿房就像一座金色的牢笼,囚禁着私生子那未知的命运;船只要是在马六甲被焚毁,婴儿房立刻改成骨灰堂,仿佛一切都没有生过,那私生子的存在就像一场虚幻的梦。
年,某艘返航船带回的不是香料,而是一封装在蜡丸里的密信:总督在爪哇娶了当地公主,私生子成了合法的“混血继承人”。
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天股价暴跌,仿佛是市场对这个荒谬结果的嘲笑。
原配夫人没掉一滴泪,只把密信投进壁炉,转身吩咐管家:“去请最好的画家,给我的长子画一幅肖像,要站在世界地图前面。”地图上的爪哇岛被墨汁涂成一个黑洞,仿佛那里从来不曾存在过,就像要抹去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到了十八世纪的圣彼得堡,连黑洞都不需要了,一切都变得更加直接和残酷。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宫廷法典干脆把“私生”定义为“可消耗资产”,将私生子的生命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
情妇们被安排住进涅瓦河畔的“玻璃宫”——外墙全由镜面组成,白天反射冬宫的金顶,夜里反射雪原的极光,唯独照不出自己的模样,就像她们在这世间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份。
而同样类似的故事也方式在一个雪夜,镜面宫里传来断弦般的尖叫,那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仿佛是命运的哀号。
女官们冲进去,只看见摇篮翻倒,炉火熄灭,雪片从敞开的窗灌进来,落在地毯上像一床碎骨,仿佛预示着这里刚刚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
情妇被吊在水晶吊灯下,脚尖还穿着缎面舞鞋,鞋尖凝着冰,就像她那冰冷而又绝望的生命。
她的丈夫——彼时正陪同女皇检阅近卫军——收到急报后,只回了六个冰冷的字:“按惯例处理。”这六个字,如同一把冰冷的利剑,斩断了情妇最后的希望。
惯例就是:把尸体装进雪橇,拉到芬兰湾,凿开冰面,连人带摇篮沉进去。
冰层合拢前,有人看见那只缎面舞鞋浮上来一次,像一枚不合时宜的浮标,旋即又被暗流拖走,仿佛是情妇那不甘的灵魂在挣扎。
于是,欧洲的家谱越翻越厚,厚到每一页背面都渗着一圈淡褐色的渍。
那其实不是墨水,而是提前支付的惨痛代价,是无数私生子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悲剧。
每一次“废嫡立幼”的风声,都会让原配、大舅哥、教区神父、账房先生,甚至远在战场的雇佣兵,同时伸手到同一只钱袋里,摸出一截绞绳、一杯毒酒,或一把冰凿,为了维护那所谓的家族秩序和利益,不惜一切代价。
私生子们还没来得及长大,名字就先被写进遗嘱的附录,又被狠狠划掉;再写进下一任情妇的诗歌,再次被无情划掉。划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冷冰冰的注脚:“倘若存在,即需抹除;倘若抹除,即从未存在。”
这便是他们那可悲又可叹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同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短暂地划过,却留不下任何痕迹,只留下一片无尽的黑暗和绝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在欧洲的纹章学里,死亡从来不是意外,而是条款。
联姻合同最后一页永远留着一行极细的哥特体小字:“若任何一方擅自撕毁婚姻意向,违约者及其直系情感关联人须以生命抵偿”。那行字被金粉勾边,看上去像装饰,实则是断头台的倒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