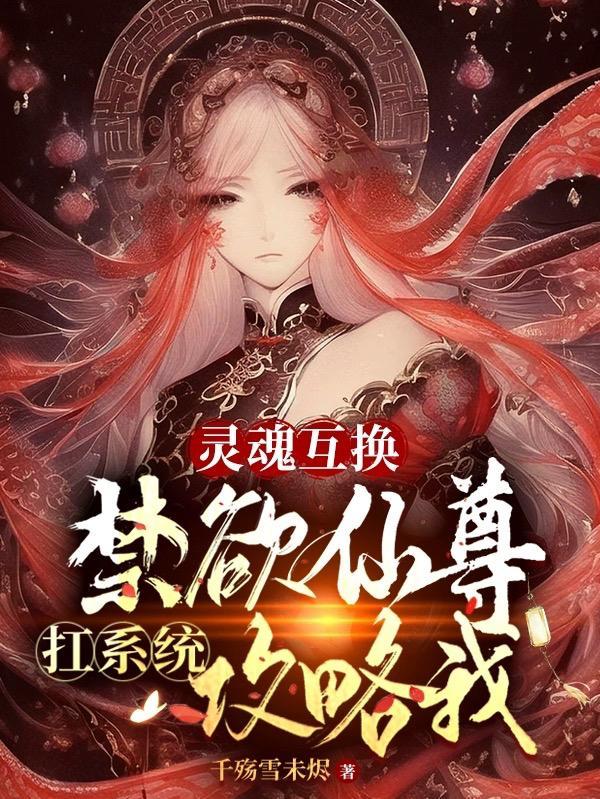91言情>见月 > 2030(第16页)
2030(第16页)
宣平侯不疾不徐,目光从陈章转向苏彦,“苏相,敢问一句,您为陛下寻药,药呢?”
“臣未取得药,途中得信,先帝崩逝,遂急行军返回。”
苏彦对殿上储君拱手道,“先帝已逝,得药无用,臣自然不会再以城池交换。”
他侧过身来,“不知这有何差错,还望宣平侯明示。”
“这自然无措,若是这等时候苏相还要以城池换之,岂不是做实了卖|国之实。
寻常人都晓得的道理,苏相麒麟之才,自然懂得。
臣要说的也不是这处。”
宣平侯看了眼殿上少女,对苏彦道,“请问苏相,您行军速度几何?此番从长到兴势郡,乃需要几日?”
披麻戴孝的少女闻此话,拢在袖中的手蓦然一紧。
苏彦亦蹙了眉,似意识到什么,转而望向江见月,却只是滞了一瞬,依旧从容道,“臣此番虽是前往签订协议,以土换药。
然为防万一,乃举兵甲而出,故而行军速度一日一百二十里。
只因出征当日即遇风雪,故而速度减缓,一日不足八十里。”
殿堂之中私语之声再度响起,尤其是常年征伐领兵的楚梁二王亦变了脸色。
只是梁王范霆自天子崩逝,便一直沉默消沉,这厢更是咬牙切切,眸中盈泪。
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了。
按照苏彦所言,即便一日行军权作八十里算,大行皇帝崩逝于十一月十六,此时他行军路程不足五百里。
而十七日报信使者从长安出,单骑速度稍快,风雪天最快可达二百里一日,如此算,追上苏彦大军,仍需四日,也就是在十一月廿方才能将信送到苏彦手中。
彼时就算苏彦轻装即刻返回,亦照二百里一日算,尚需四日,乃十一月廿四。
然而苏彦十一月廿已经抵达长安。
换言之,乃先帝未崩之时便已折返。
其心何意?
其心可诛!
满殿目光,皆投苏彦处。
苏彦目光从少女身上飞速而过,见得她面色惨白,鬓角滴汗,整个人僵硬着喘息,鲜为人见的麻衣袖沿,已经出现褶皱痕迹。
是因为她攥着中衣袖角,掌心皮肉抠破,胃里翻涌绞痛。
在数月耗尽心力的谋划里、在数日守着父亲尸身的坚守里、在这一刻突发的情境里,重压和惶恐漫天袭来,又开始发病。
她当日谴人送信,本就是兵行险招。
但彼时江怀懋已经一连缠绵病榻十数日,太医亦言定要静卧,不可离榻。
她便想着反正群臣百官已经见不到他,甚至因为医嘱之故,陈婉母女都极少来此,偶有一趟亦被范霆在夷安进言下被赶走。
他何时崩逝且自己说了算。
但却事出意外,初雪宫宴上,江怀懋竟然出现在群臣面前,让她彻底乱了分寸。
眼看苏彦越行越远,她只得孤注一掷,择了当晚行事。
她终是年少,少了历练和经验,竟然忽略了此间时辰差。
即便这一刻醍醐灌顶反应过来,但俨然已经来不及。
若是私下里,她可以和苏彦说,是父亲之意,深感大限将至,已是等药不及,让他从大局看,速归以护幼主。
若她这般主动言之,以苏彦对她的情意,定然是相信的。
然此时此刻,在这父亲梓宫前,葬仪上,被一个已经为人遗忘的宣平侯掀上台面。
直接成为一把捅向苏彦的刀。
一盆他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的污水。
无比被动。
江见月浑身都在抖,当下她依旧可以如此言,群臣也未必不信。
但是苏彦呢,是否会不再完全信任她,会不会不再偏爱偏护她?
她曾因母仇,算计过他一次。
然而那一次,有苍生黎民在前,他心甘情愿入局中,甚至觉得还是他自己的优柔徒增了伤亡。
然而这次呢,她要如何让他一如既往信任自己?有何人何事,能再度挡于她之前,然他觉得自己非但无错,还无奈!
杀弟,逼父,图谋,夺权……寻不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寻不到不是为了自己的理由!
但却是唯一的理由。
她就是为了自己,为活着!
成王败寇,何论对错。
思至这处,她竟是挺直了背脊,坦然又平静地对上了苏彦再度投来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