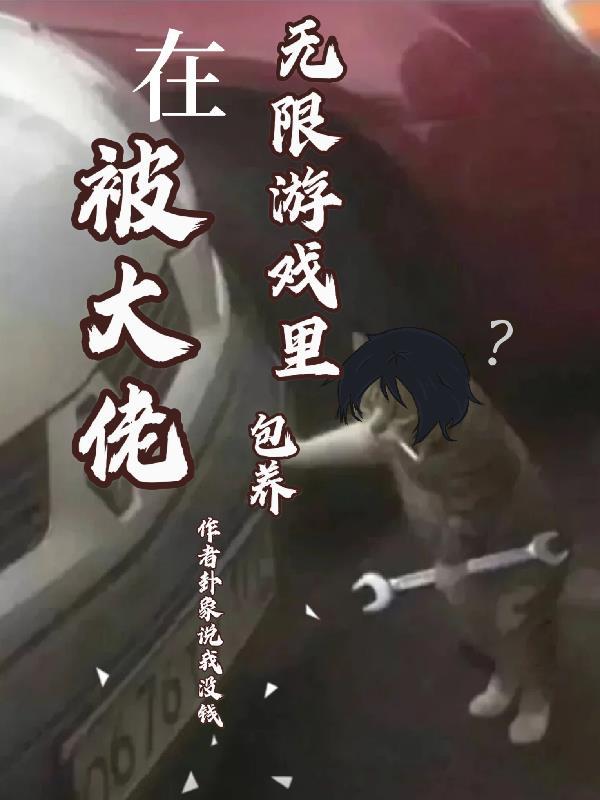91言情>同袍 > 第 27 章(第2页)
第 27 章(第2页)
“是声东击西。”萧砚之突然明白过来,谢清辞早就让孩子们绕去了侧翼。最後五名兵卒分神的瞬间,他的短刀已刺穿两人的咽喉,谢清辞的铜剪则绞住了第三人的脚踝,将人硬生生拽进盐沼,惨叫声在空旷的滩涂里格外瘆人。
剩下的两名兵卒突然跪地求饶,其中一人的护膝上印着个模糊的“谢”字——是当年从染坊被强征的学徒,左手食指缺了截,是染布时被铜剪误伤的旧痕。谢清辞的剪尖停在他咽喉前,指腹摩挲着剪柄上的刻痕,那是他亲手刻的染坊记号。
“滚。”谢清辞的声音很轻,铜剪却突然转向,刺穿了另名兵卒的心脏,“告诉狼旗,染坊的账,我会亲自去鹰嘴崖算。”那名学徒连滚带爬地跑了,铁甲陷在盐沼里的声响越来越远,萧砚之看着他消失的方向,突然发现盐沼的白霜上,印着串带血的脚印,像幅被踩脏的白描。
千夫长的尸体在红树林的火海里发出爆裂声,谢清辞靠在礁石上,小腿的血正往盐沼里渗,将那片白霜染出点点暗红。萧砚之撕下衣襟给他包扎,指尖触到对方小腿骨的凸起,才惊觉那处骨头竟有些变形——是去年箭楼火里被重物砸的旧伤。
“疼吗?”他的声音发颤,布条在手里打了个死结。谢清辞突然笑出声,染蓝的指尖戳了戳他渗血的肩头:“比你当年在染坊打翻苏木缸,把我新染的蓝布染成紫的那天,轻多了。”
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叫,阿竹举着面新染的红旗奔过来,旗面在风里猎猎作响,是用狼旗的布料改染的,边缘还留着被铜剪挑破的缺口。萧砚之扶着谢清辞站起来,两人交握的手腕上,靛蓝布条已被血浸成深紫,却仍牢牢缠着,像两道拧在一起的血脉,往鹰嘴崖的方向延伸。
盐沼的尽头,晨曦正漫过鹰嘴崖的轮廓。谢清辞突然低头,将掌心的油菜籽撒在盐沼里,那些沾着血的嫩芽落在白霜上,竟没被冻住,反而抖了抖叶片。萧砚之看着那些倔强的绿意,突然想起染坊後院的那片蓝草,无论被踩倒多少次,总能从石缝里钻出新芽。
“走吧。”他拽紧谢清辞的手,感觉对方的脉搏透过布料传来,和自己的心跳渐渐合拍。红树林的烟火在身後腾起,像染坊竈膛里的火,烧得正旺。萧砚之知道前路的硬仗才刚刚开始,狼旗的主力仍在鹰嘴崖等着,可只要这人的手还在自己掌心里,只要那些从血里钻出来的种子还在发芽,就没有什麽能挡住他们——
挡住这两个要在北境染出万里晴空的人。
盐沼边缘的风突然转向,卷来鹰嘴崖方向的号角声,沉闷如染坊蒸布的木甑。谢清辞突然按住萧砚之的肩,指腹在他伤口处轻轻打了个结——那是染布时固定布角的手法,松紧得恰好能止血又不碍动作。
“他们在集结。”谢清辞望着崖顶飘动的狼旗,铜剪在掌心转了个圈,“千夫长的死该传到主营了。”他突然拽着萧砚之往盐沼深处走,软泥没过膝盖的阻力里,萧砚之看见对方小腿的血珠坠在泥里,竟让那些灰白的盐碱地透出点青黑,像极了染坊里未洗净的媒染剂。
孩子们的身影在盐沼尽头的沙丘後晃动,阿竹举着的红旗突然向下压了压——那是谢清辞教的旗语,意为“有埋伏”。萧砚之的短刀刚出鞘,沙丘後已滚出十馀只铁笼,笼里的狼崽嗷嗷直叫,铁链拖地的声响惊得盐沼里的水鸟扑棱棱飞起。
“是狼旗的驯兽兵。”谢清辞突然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染坊的硫磺粉,“捂住口鼻。”他将粉末往逆风处撒去,硫磺遇水蒸腾起的黄雾里,驯兽兵的咳嗽声此起彼伏。萧砚之趁机掷出短刀,刀柄撞在铁笼的锁扣上,受惊的狼崽猛地扑向笼外的兵卒,獠牙撕开皮肉的声响里混着惨叫声,格外刺耳。
最左侧的驯兽兵正解另只铁笼的锁链,谢清辞的铜剪突然飞出去,剪尖缠住对方的手腕往回拽。那兵踉跄着扑进盐沼,铁甲陷进软泥的瞬间,萧砚之已踩在他肩头跃起,短刀刺穿了另名兵卒的咽喉。下落时靴底沾着的盐碱粒蹭在对方护心镜上,划出的白痕像极了染布时银线勾的暗纹。
“阿砚看笼底!”谢清辞突然拽着他後跳,铁笼底部的尖刺正随着锁链收缩向上弹起,是北境特有的“狼吻”机关。萧砚之反手将短刀插进最近那只铁笼的缝隙,刀刃撬开底板的瞬间,看见笼里铺着的黑布——浸过狼血的料子,难怪能镇住这些狼崽。
驯兽兵的头目突然吹起骨哨,剩馀的狼崽竟齐齐转向扑来。谢清辞拽过条拖在地上的铁链,手腕翻转的弧度像在搅染缸,铁链突然绷直缠住最凶那只狼崽的脖颈,借力往回带的瞬间,狼崽的獠牙正好撕在追来的兵卒脸上。
萧砚之的短刀卡在狼崽的肋骨里,盐沼的泥水溅了满脸,咸涩味钻进鼻腔时,他突然想起去年暗河底的水草缠住脚踝的触感。谢清辞的铜剪已旋过两名驯兽兵的咽喉,剪尖挑落的骨哨坠在泥里,发出沉闷的嗡鸣,像染坊漏风的风箱。
最後一只狼崽被铁链勒断脖颈时,盐沼里已积起层暗红。谢清辞靠在铁笼上喘气,小腿的伤口在泥水里泡得发白,却仍死死攥着那把染坊的铜剪,剪尖沾着的硫磺粉遇血凝成黄痂,像极了染坏的栀黄绫。
“还有三里到鹰嘴崖的栈道。”萧砚之撕下衣角擦他脸上的泥,指尖触到对方耳後新结的痂,“孩子们呢?”
“阿竹带他们从密道绕去栈道尽头。”谢清辞突然笑出声,染蓝的指尖戳了戳他胸口,“你当年藏在染坊地窖的那箱火药,我让他们擡去了。”
萧砚之突然想起那箱硝石,是去年准备给新染坊炸地基用的。风里传来铁蹄声,比千夫长的队伍更沉,是狼旗的重骑兵。谢清辞突然拽着他往盐沼边缘的矮树丛钻,那些带刺的枝条刮过衣襟,将靛蓝色的布料勾出细痕,像极了染布时被木刺勾破的料子。
重骑兵的铁蹄踏在盐沼边缘的硬地上,甲胄碰撞的脆响里,萧砚之听见为首者的怒吼——是狼旗的万户长,当年火烧箭楼的主谋。谢清辞突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染坊的石绿粉,他将粉末往骑兵的方向撒去,石绿遇风扬起的绿雾里,那些战马突然惊嘶着人立起来。
“北境马怕这颜色。”谢清辞拽着他往栈道方向跑,“去年在染坊试过,石绿染的幡子能镇住受惊的马。”重骑兵的混乱里,两人钻进了鹰嘴崖的栈道,木质的栈道板踩上去咯吱作响,像染坊年久失修的晾布架。
栈道外侧的悬崖下是暗河,涛声里混着狼旗主力的呐喊。谢清辞突然拽着他躲进栈道旁的石窟,里面竟堆着些染坊的旧料——是去年搬来的苏木和紫草,被他藏在这里做应急的染料。万户长的怒吼从栈道那头传来,带着铁蹄踏木的震颤。
“把这些料子往栈道上撒。”谢清辞突然将半包苏木粉塞进他手里,“苏木遇潮发滑,铁甲踩上去准打滑。”萧砚之刚将粉末撒出去,重骑兵的铁蹄已碾到眼前,最前那匹战马果然打滑,骑手摔出栈道的惨叫里,万户长的长柄刀已劈进石窟。
谢清辞拽着他往石窟深处退,岩壁上的钟乳石划开後背的伤口,血珠滴在紫草堆里,让那些暗红的草料透出点紫黑,像极了他调的“墨紫”色。万户长的刀再次劈来时,萧砚之突然将怀里的油菜籽往对方脸上撒去,那些发了芽的种子钻进对方眼里,惨叫声里,谢清辞的铜剪已刺穿他的手腕。
“记不记得染坊那口老井?”谢清辞突然笑出声,拽着万户长往石窟内侧的暗洞退,“你当年把谢家族人绑在井边,也是这样举着刀。”暗洞的石壁突然向外倾斜,万户长的铁靴踩在松动的石块上,整个人往悬崖下坠去的瞬间,萧砚之看见他腰间的玉佩——谢家祖传的染坊令牌,被硬生生凿去了“谢”字。
铜剪旋即绞住对方的手腕,谢清辞的臂力竟让下坠的势头顿住。万户长的嘶吼里带着难以置信,萧砚之突然想起去年在染坊,这人也是这样攥着根浸了蓝草汁的麻绳,将掉进染缸的阿竹从三米深的缸底拽上来。
“你该还账了。”谢清辞的声音很轻,铜剪突然转向,剪断了对方的手腕筋。万户长坠下悬崖的惨叫里,萧砚之看见他染蓝的指尖在发抖,却死死攥着那枚被凿坏的令牌,指腹反复摩挲着残缺的边缘。
栈道那头突然传来孩子们的欢呼,阿竹举着的红旗在崖顶展开,像团烧旺的火。谢清辞靠在石窟壁上,小腿的血正往紫草堆里渗,将那些草料染得愈发浓重。萧砚之突然拽过他的手,将那粒沾着两人血的油菜籽按在他掌心的令牌上,血珠立刻将嫩芽裹住,像给这枚残缺的信物缀了点新绿。
“你看。”萧砚之的拇指蹭过他染蓝的指节,“就算被凿坏了,也能长出新东西。”
谢清辞突然笑出声,眼泪混着石绿粉往下淌,在脸颊上冲出两道绿痕,像极了染坏的翡翠绫。远处的暗河上飘来片靛蓝色的帆,是染坊的旧船,阿竹正带着孩子们往这边划,帆面在风里展开的弧度,像极了当年他们在染坊晾晒的第一匹蓝布。
栈道的木板在脚下咯吱作响,两人交握的手腕上,靛蓝布条已被血浸成深紫,却仍牢牢缠着。鹰嘴崖的风卷着硝烟掠过耳畔,萧砚之看着崖顶飘动的红旗,突然明白那些从血里钻出来的种子,那些在伤口上开出的纹样,从来都不是结束——
是染坊的新颜色,是家国的新料子,是他们要在北境的土地上,染出的万里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