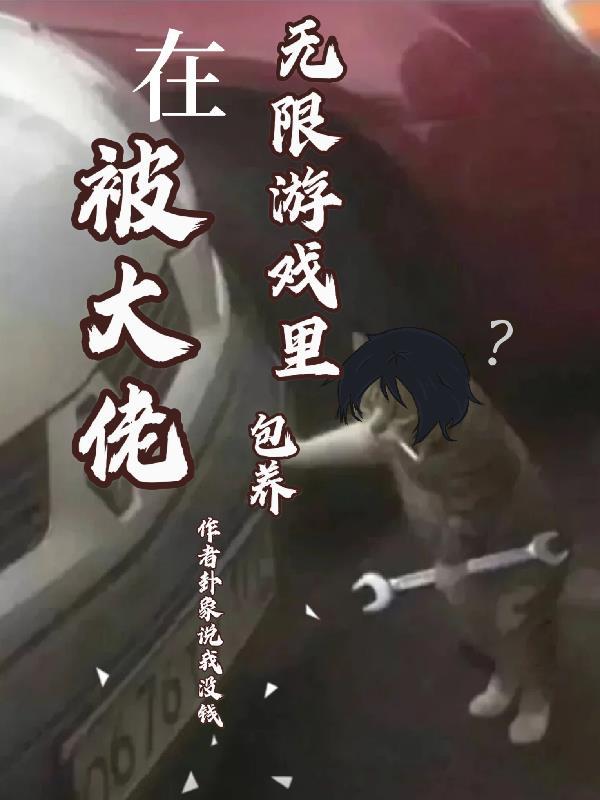91言情>她是养猪的 > 40 她的主子被人拱了(第1页)
40 她的主子被人拱了(第1页)
40她的主子被人拱了
蜡烛渐短,燃尽的瞬间好似发出了微弱的嗡鸣。
手下的温度好似越来越烫,阮娘撑起身子,低唤:“茶茶。”
馀茶的“嗯”声很微弱,仿佛受伤的小猫在呜咽一般,听得阮娘心里一紧。
她往上爬了爬,拿湿漉漉的手往被褥上随意一擦,然後摸上馀茶的额头,微烫,她又低下头,额头贴额头,脸颊贴脸颊,还是烫。
“茶茶,你高烧了,我……我去找大夫。”
阮娘懊悔极了,她觉得馀茶此次高烧是她太不知节制了,一遍又一遍,从蜡烛初燃,到油灯尽灭。
初尝情事的人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把发誓要捧在手心里的人弄病了。
阮娘慌里慌张地捞过床尾的衣裳匆匆披上,连衣带都未曾系牢便冲出房间,拍响小小的房门,“小小,茶茶高烧了,你快去请白大夫,小小,小小,快去请白大夫……”
身为馀茶的贴身丫鬟,小小即使睡着也带着两分警觉,在阮娘拍响第一声房门时,她便睁开了眼,又一听主子高烧了,当下穿着里衣冲了出去。
但她一眼便看见夫人脖子上的咬痕,一向以稳重自持的小小差点尖叫起来。
——她的主子被人拱了!!!
小小拧成麻花一样的肠子愣是被这个咬痕捋直了,一言难尽地看着自家神情慌张的夫人,然後一声不吭地跑出去再次把白大夫从床上拖起来。
衣衫不整的两人来到馀茶房间时,脚步微微顿了下,脸颊也跟着微微发红起来。
“白大夫,你快来给茶茶看看,她烧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阮娘无心注意她们是不是因空气弥漫的味道而感到羞涩,她捏着白静殊的衣袖往里拽,嘴里紧张道:“茶茶她发了很多冷汗,人也迷糊了,怎麽办呀?”
白静殊努力忽视心里的别扭,手指搭上那只纤白的手腕上。
好一会儿後,白静殊手指微微一颤,她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最後才想起自己是个大夫,理应摒弃羞耻。
她直言道:“小姐身子弱,经不住太大的折腾,像行房这种事,理应节制,初夜应当浅尝辄止才是。”
闻言,小小呆呆望着一脸‘正直’的白静殊,心想:这妮子为何总这般不懂委婉?继而瞪向自家夫人,心里开始骂人。
是她没能抵住诱。惑,阮娘坐在床边替馀茶擦着汗,她一直都不大红的唇在今晚却有些诡异的粉肿,脸色也白得像外面的月亮,身体时而颤抖一下,处处都在昭示着她的罪行。
阮娘感觉心里像藏了一粒山茱萸般,被馀茶泡得又酸又涩。
她从小小手上接过汤药,却被瞪了一眼,阮娘没心情应付她,接过药挥手让她出去烧点热水。
“茶茶,喝了药再睡吧。”阮娘把馀茶扶起来靠在肩头。
馀茶已经烧得理智逐渐离家出走,做事全凭本能,这道苦涩的药味刚一被人送进嘴里,她便感到一阵委屈,想吐,又觉得不雅,含在嘴里,又将她的舌头苦得麻麻的,吞下,又觉不甘。
怎麽都不对,憋得她淌出了眼泪。
阮娘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馀茶,拿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瞪人的样子就像只小奶猫似的,乖软可爱。
她心头软软,哄道:“茶茶乖,把药吞下去好不好,喝了药才能好,喝完药明天就给你煮甜甜的汤圆吃。”
烧迷糊的馀茶很乖,她连委屈都只会安安静静地瞪人,被人一哄,就什麽都照做。
喂完药,阮娘又替她擦了擦身体,刚欢好过的痕迹是跌入她心里的山楂,全是酸涩。
夜里馀茶呢喃着冷,阮娘便将自己剥光抱紧她,盖上被子,不一会儿便被热出了汗,但馀茶却好似很冷,不住往她怀里拱着。
两道生涩的灵魂,第一次交融便闹出这般大的动静,她们一个纵容,一个放纵,最後却以另一种筋疲力竭的方式过完今夜。
天方初亮,阮娘便捧着一碗白粥进房了。
她一夜未睡,不时给馀茶探温,替她擦汗,确保她的身体保持干燥,好在在天边破晓时,她的体温回到了正常温度。
馀茶瞥一眼那碗白粥,又看向阮娘,眼里似有委屈,看得阮娘一脸莫明,她放下白粥,擡手往馀茶额头探了探温,“退烧了呀,茶茶不爱喝白粥吗?”
说完,她又哄道:“可是白大夫说要吃清淡的,咱们先吃两顿白粥好不好?”
她好似不容人拒绝,舀着白粥就喂了过来。
馀茶瞪她,“你昨夜说会给我煮汤圆吃。”
不等她胡思乱想地给她按罪名,阮娘赶忙解释,“我记着呢,但你昨夜吐了不少,白大夫说早上最好吃点白粥,我们下次再煮汤圆好不好。”
昨夜馀茶烧得迷糊,只觉胃里难受,後半夜便开始呕吐,如今她想起点模糊的记忆,脸上不由变得粉粉的。
阮娘张了张嘴,馀茶先她一步开口道:“那便先吃白粥吧。”
可爱。
阮娘一笑,柔顺地给她喂着粥,末了又探了探她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