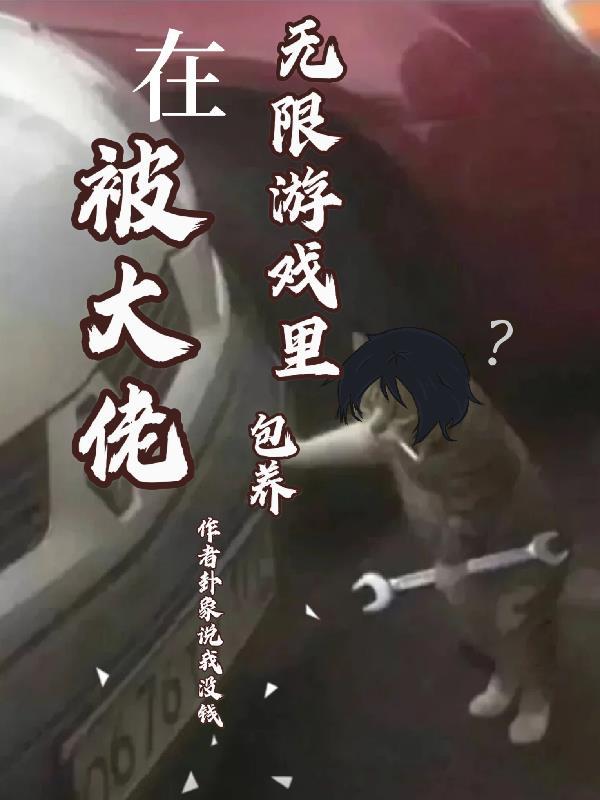91言情>尸匠 > 第48章 万里挑一(第2页)
第48章 万里挑一(第2页)
“患难与共,生死不离。”杨望重复了一遍,美滋滋地品鉴着其中含义:“娘子对我如此痴心,我必不负你,呜——”
“我只是权宜之计,你听听就好,不必当真。”沈峥抓起案上一块茶点,快步上前塞进他的嘴里,还想再威胁他不准再提此事,忽地瞥见他身上的伤痕。
不仅是那道触目惊心的刀伤,杨望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些地方的皮肉已经肿胀渗血,就连他两只手也因挖掘废墟变得伤痕累累。沈峥讶然握住他的手,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她不敢相信,这个世上,怎麽会有人心甘情愿为她做到这种地步?
“我没事的。”杨望见她面露复杂之色,连忙抽回手缩进衾被里,将身上的伤包裹的严严实实,“真的,你别担心,我从小体格就好,外出狩猎一天一夜都不会累,就这点小伤,根本不在话下。”
“我骗了你。”
沈峥打断他,一脸肃穆地看着他:“我爹根本不是被仇家害死的。十年前,台州府长亭县惨遭海寇屠城,我爹被海寇活活砍成尸块,三万百姓血流成河,我是唯一幸存者。”
杨望一时有些错愕,不知该说什麽,只能等着沈峥继续说。
“这一路来,我都在寻找当年血案的罪证。有了罪证,我便可以为我爹和三万长亭百姓洗清冤屈。”沈峥从怀里掏出一张信纸,“就在今日,这个罪证,我拿到了。”
她紧攥着那张纸,却迟迟不肯打开。十年前的种种血色记忆,仿佛这场骤雨般,密密麻麻丶狠狠敲击着她的心。那一瞬,她竟有些明白许栋的心情了。在绝对的真相面前,她们是如此渺小,以至于连这薄薄一张信纸的重量都难以承受。
又或者说,即使揭露了这个真相,她真能如许栋一般坦然的面对吗?
就在她怔怔出神时,杨望忽然一把抢走了那张纸。
“哎,你!”沈峥一愣,伸手就要去夺,被他侧身躲开。
“既然这张纸上的真相那麽重要,那就打开看看啊!”杨望低头盯着上面的字迹,“我倒想知道,到底是什麽折磨了你十年,让你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甚至连一件好看的衣服都舍不得穿!”他说到後面,已经咬牙切齿,带着和这东西较劲的意味了。
可当杨望通篇读完,神情却渐渐变得困惑,最後擡起头,茫然地看向沈峥:“你确定这就是罪证?”
沈峥心里涌上一股莫大的不安,夺过信纸展开。
“通火辟疫汤?”沈峥愕然读出方名。
尽管开篇就已经是当头一棒,她仍抱着一丝希望,慢慢往下读。这药方上的字因为时隔久远难辨笔锋,而且通篇都是晦涩术语,她看了好一会,解读出大概意思:
吾近日察看疫病之势,只觉邪气炽盛,白日炎热,夜间反复,久治不愈,尤为影响肝胆之气。台州百姓出现痰湿郁结丶精神混乱之状。有人外感寒邪却内里发热,有人面色红润却目光呆滞。
因此,吾将重拟《通火辟疫汤》一方,意在清上导下丶调和肝脾丶安定神志。若使用远志丶冰片和胆楠星三昧中药,方能使气机通畅丶神志清宁,根除此疫。
沈峥读了一遍不够,又反复看了几遍,终于折起信纸,木然地坐在榻沿。
这怎麽可能?她苦苦追寻十年的罪证,居然只是一封治疗时疫的药方?
为了这封药方,害得她多次遇险不说,还逼迫潜藏多年的李琼连杀三人,不惜暴露身份也要藏匿?
世上怎会有如此荒诞之事?
沈峥盯着手里这张毫无价值的废纸,眼神复杂。
这时候,杨望忽然提了一嘴:“那个许栋临死前喊的名字,叫周。。。。。。周什麽来着?”
“周笑芳。”沈峥木讷地盯着眼前地砖,思绪全不在此。
“对,就是这个周笑芳!”杨望掀开被子,往前挪了挪,盘腿坐在沈峥身边,“我听这名字特别耳熟,我记得我娘曾经提过这个人。”
沈峥擡眼示意他继续说。
杨望简略讲了讲谢耘当年经历的事,“後来我娘从寇营死里逃生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夜间时常梦魇,听她的贴身婢女梧桐说,我娘有时会在梦中叫出这个名字,周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