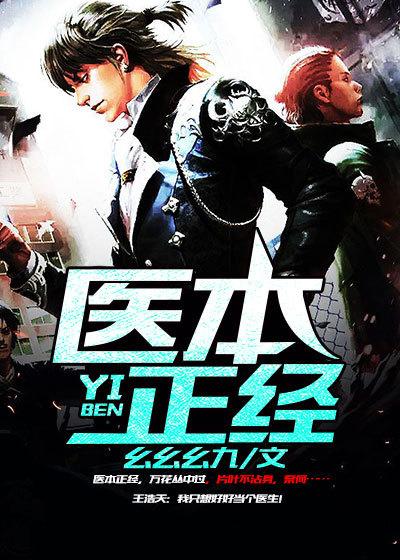91言情>星光重启:爱意系统助我逆天改命 > 第131章 新星导演计划 第五部作品聚焦城市打工者(第1页)
第131章 新星导演计划 第五部作品聚焦城市打工者(第1页)
上海松江的电子厂门口,傍晚六点的铃声刚响,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们便陆续走出厂区。岁的李娟习惯性地从背包里掏出写本,蹲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快勾勒着夕阳下工友们疲惫却鲜活的身影——她笔下的线条没有精致的修饰,却满是生活的温度。这一幕,被正在采风的新人导演陈雨用相机定格,后来成为电影《城市之光》开篇最打动人心的镜头之一。
作为“新星导演计划”扶持的第五部作品,《城市之光》从筹备之初就带着“反套路”的初心。当市场上的现实主义电影多聚焦“中产焦虑”“家庭伦理”时,林晚星却力排众议,支持陈雨将镜头对准“城市打工者”这一常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很少有作品真正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拍的不是‘卖惨’的故事,而是他们在生存之外,对艺术、对梦想的渴望——那些藏在流水线、外卖箱、工地安全帽下的热爱,才是最动人的‘城市之光’。”
从深入打工者社区采风,到邀请真实打工者参与创作,再到上映后引社会对“打工者精神文化需求”的讨论,《城市之光》用最朴素的叙事,完成了一次对“平凡梦想”的致敬。最终,这部投资仅ooo万的小成本电影,收获了亿票房与分的豆瓣高分,不仅成为“新星导演计划”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更被中国电影家协会评为“年度现实主义佳作”,证明了“关注平凡人,也能拍出有力量的好电影”。
“新星导演计划”自启动以来,始终以“扶持新人、挖掘多元题材”为核心。前四部作品涵盖了青春校园、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领域,而第五部作品的选题,却让团队陷入了争论——有人建议延续“安全牌”,选择观众熟悉的家庭题材;有人提出尝试悬疑类型,迎合市场热点。直到陈雨带着《城市之光》的剧本走进林晚星的办公室,这场争论才有了答案。
陈雨的剧本,源于她三年前的一次偶然经历。当时她在深圳的城中村租房,邻居是一对在电子厂打工的情侣:男孩每天下班后会在阳台弹吉他唱歌,女孩则喜欢用捡来的废纸箱画画。“有一次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艺术?男孩说,‘在流水线上站了十个小时,只有弹吉他的时候,才觉得自己不是机器,是活生生的人’。”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陈雨,也让她萌生了“为打工者拍一部电影”的想法。
剧本里的三个主角,都有真实的原型:在电子厂打工的“晓雅”,原型是喜欢画画的李娟;白天送外卖、晚上在街头唱歌的“阿明”,来自陈雨认识的外卖员王哥;在工地干活,却偷偷练街舞的“大强”,则是她在采风时遇到的后工人。“我不想塑造‘完美的梦想家’,而是想展现他们的‘矛盾与挣扎’——晓雅怕被工友嘲笑,只能在厕所偷偷画画;阿明想参加选秀,却担心年纪太大;大强的父母觉得跳舞是‘不务正业’,多次劝他回家。”陈雨说,“这些真实的困境,才是打工者追求梦想时最真实的样子。”
林晚星在看完剧本后,当即决定全力支持:“这个剧本最打动我的,是它没有把‘艺术’塑造成‘脱贫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精神的出口’。晓雅画画不是为了成名,只是为了记录生活;阿明唱歌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抒情绪。这种‘不为功利的热爱’,比任何‘逆袭故事’都更有力量。”
为了让电影更贴近真实,林晚星要求陈雨团队用三个月时间,深入长三角、珠三角的打工者社区采风。他们住进电子厂附近的出租屋,跟着外卖员跑单,在工地和工人一起吃盒饭,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流水线操作——每一个细节的积累,都成为电影里“真实感”的来源。
在电子厂采风时,团队现工人们的“业余生活”远比想象中丰富:有人在宿舍用手机剪辑短视频,有人组织了“打工者读书会”,还有人用工厂废弃的零件制作手工艺品。“这些细节都被我们写进了剧本,”陈雨说,“比如晓雅用工厂的油性笔在写本上画画,笔没水了就用口红代替;阿明的外卖箱里总装着一个便携麦克风,接到订单少的时段,就找个没人的街角唱两。这些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而是真实生在打工者身上的事。”
最让团队意外的是打工者对“声音”的敏感。在工地采风时,他们现工人会用钢筋敲击的节奏、塔吊转动的声响,编出简单的“劳动号子”;在快递分拣中心,分拣员会根据包裹掉落的不同声音,判断包裹里装的是什么。“这些‘工作场景中的声音’,后来成为了电影配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指导张远说,“我们邀请了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打工者,用他们熟悉的工具创作节奏——电子厂的零件碰撞声、外卖车的刹车声、工地的电钻声,经过改编后,变成了既独特又充满生活气息的配乐,比传统的交响乐更有感染力。”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城市之光》的拍摄过程,始终围绕“真实”二字展开。从演员选择到场景搭建,从镜头语言到台词设计,陈雨团队拒绝“戏剧化的夸张”,坚持用“克制的叙事”展现打工者的生活与梦想。林晚星更是多次亲临片场,强调“不要为了煽情而煽情,要让情感自然流露——打工者的梦想,不需要用眼泪证明,需要用细节打动”。
在演员选择上,团队放弃了邀请流量明星的想法,转而启用“新人演员+真实打工者”的组合。饰演晓雅的演员张婷,是从打工者社区选拔出来的——她曾在电子厂工作过两年,不仅会画画,更懂晓雅“想隐藏热爱又忍不住追求”的矛盾心理;饰演阿明的演员王浩,是酒吧驻唱歌手,有过送外卖的经历,他在街头唱歌时的“松弛感”,是专业演员难以模仿的;而饰演大强的演员李阳,则是街舞爱好者,他在工地宿舍练舞的场景,几乎是“本色出演”。
“我们选演员的标准不是‘演技多好’,而是‘像不像’,”陈雨说,“有一场戏,晓雅在厕所画画被工友现,她下意识地把写本藏在背后,手指紧张地抠着衣角——这个动作不是剧本设计的,是张婷在拍摄时自然流露的,因为她在电子厂时,也曾因为画画被工友嘲笑过。这种‘源于生活的真实反应’,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表演都更有力量。”
团队还邀请了o多位真实打工者参与群演。电子厂流水线的工友、外卖站点的骑手、工地的建筑工人,他们没有表演经验,却用最自然的状态,还原了打工者的生活场景。“有一场晓雅和工友在食堂吃饭的戏,群演们不用导演指导,就自然地聊起了‘今天产量多少’‘周末去哪玩’,那种热闹又带着疲惫的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陈雨回忆道,“拍完那场戏,我跟林总说,‘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电影’。”
《城市之光》的场景搭建,拒绝“精致化的还原”,坚持“从生活中来”。电子厂的车间是租下的废弃工厂,团队按照真实电子厂的布局,重新安装了流水线设备,连工人们工装的款式、安全帽的颜色,都与真实电子厂一致;晓雅住的出租屋,是在城中村租的真实房间,墙上贴着打工者喜欢的明星海报,桌上摆着用了一半的护肤品,甚至连床底下堆着的行李箱,都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努力贴近打工者的真实生活。
镜头语言则以“克制、平实”为主。拍摄流水线场景时,导演没有用夸张的快节奏剪辑,而是用长镜头记录晓雅重复的工作动作,从清晨到傍晚,镜头慢慢移动,展现时间的流逝与工作的枯燥,为后续“晓雅在画画中寻找解脱”做铺垫;拍摄阿明街头唱歌的场景时,镜头从远处慢慢推进,先拍路人的冷漠与匆匆,再聚焦到阿明投入的演唱,最后定格在听完歌后默默扫码打赏的老人身上——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观众感受到“平凡人之间的温暖”。
“林总曾跟我说,‘现实主义电影的镜头,应该像打工者的眼睛,真实地看到生活的样子’,”陈雨说,“所以我们很少用华丽的镜头技巧,更多的是用‘平视’的角度去拍摄——不俯视,不仰视,只是客观地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梦想。这种‘朴素’的镜头语言,反而更能传递出温度。”
《城市之光》的台词,拒绝“书面化的表达”,坚持“从打工者的口中来”。团队在采风时,记录了大量打工者的真实对话,经过整理后融入剧本——晓雅跟工友说“画画能让我忘了站了一天的累”;阿明跟顾客解释“晚了十分钟,路上堵车,不好意思”;大强跟父母打电话说“我在这边挺好的,你们放心”——这些简单、直白的台词,没有复杂的修辞,却充满了生活的质感。
最打动观众的一句台词,来自电影的结尾:晓雅在打工者艺术展上,看着自己的画被展出,对身边的阿明说,“以前觉得画画是偷偷摸摸的事,现在才知道,我们的生活,也能被看见”。这句话不是编剧凭空写的,而是来自真实打工者李娟的心声——在采风时,李娟曾对陈雨说,“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过客,没人会在乎我们喜欢什么,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画能被人看见,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了”。
“这句台词没有喊口号,却说出了很多打工者的心声,”林晚星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台词,让观众意识到,打工者不仅有生存的需求,还有被看见、被尊重的精神需求——这才是电影想传递的核心。”
《城市之光》上映前,很多人不看好这部“没有明星、题材小众”的电影,甚至有院线经理建议减少排片。但林晚星坚持“相信观众的判断力”,联合全国oo多家影院,开展“打工者专场”放映活动,邀请打工者免费观影。没想到,正是这些“小众”的专场,引了口碑的酵——看完电影的打工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故事,带动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最终让《城市之光》实现了“票房逆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城市之光》上映后,最热烈的反响来自打工者群体。在深圳的一场“打工者专场”放映结束后,一位外卖员站起来说,“阿明在街头唱歌的样子,像极了我——我每天送完外卖,也会在公园唱两,不是想当歌手,只是想让自己放松一下。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我的热爱不是没用的”;一位电子厂女工说,“晓雅在厕所画画的场景,我也经历过,怕被别人笑,只能偷偷地画。看完电影,我决定明天就把画本带到车间,想画的时候就画”。
这些真实的反馈,让陈雨和林晚星既感动又意外。“我们原本只是想拍一部电影,没想到能给打工者带来这么大的勇气,”陈雨说,“有位打工者给我消息说,‘因为这部电影,我报名了社区的绘画班’,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为了让打工者的艺术梦想得到更多支持,林晚星还联合公益组织,起“城市之光艺术计划”——在全国o个城市的打工者社区,建立“艺术空间”,提供绘画、音乐、舞蹈等培训课程;同时举办“打工者艺术展”,让打工者的作品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电影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们希望能通过后续的公益行动,让更多打工者感受到,他们的梦想值得被尊重、被支持,”林晚星说。
《城市之光》不仅收获了打工者的共鸣,也得到了普通观众与电影行业的高度认可。豆瓣分的评价中,有观众留言“这是今年最打动我的电影,没有之一——它让我看到了城市里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那些平凡人身上的光”;有影评人评价“《城市之光》没有刻意制造冲突,没有强行煽情,只是用真实的细节,讲述了一个关于梦想与热爱的故事,这种‘克制的现实主义’,是当下电影市场最需要的”。
中国电影家协会在授予其“年度现实主义佳作”时,评价道:“《城市之光》聚焦城市打工者这一特殊群体,用真实的叙事、温暖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在生存之外的精神追求,不仅填补了现实主义电影在该题材上的空白,更引了社会对‘打工者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这部电影还引了社会层面的讨论。《人民日报》表评论文章《关注打工者的“精神角落”》,指出“城市在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打工者的物质生活,更要重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他们提供艺术培训的空间,为他们的梦想搭建展示的平台,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多地政府也因此出台政策,在打工者社区建设“文化活动室”,开展“打工者艺术节”,让电影中的“城市之光”照进现实。
当《城市之光》票房突破亿,“城市之光艺术计划”覆盖全国o万打工者,中国电影家协会为其颁“年度现实主义佳作”奖项时,林晚星正在上海参加“打工者艺术展”——展厅里,晓雅原型李娟的画作《流水线的夕阳》挂在显眼位置,旁边围满了观看的观众;不远处,阿明原型王哥正在弹吉他唱歌,台下的打工者跟着旋律轻轻哼唱。这时,她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检测到宿主主导的“新星导演计划”第五部作品《城市之光》取得显着成效,真实展现城市打工者生活与梦想,引社会对打工者精神文化需求的关注,获得行业与社会高度认可,触“城市打工者主题电影成功”奖励。】
【获得奖励:积分点、爱意值点(来自中国电影家协会表彰、观众好评、公益组织认可)。当前剩余生命值:o天小时(此前天小时+天=o天小时)。】
【解锁新任务:【年内,推动“城市之光艺术计划”升级为“全国打工者文化扶持项目”,联合o个省市的文化部门,在o个打工者社区建立“文化服务中心”;同时,启动“打工者影像计划”,扶持打工者拍摄自己的纪录片,让更多打工者的故事被看见、被传播】,任务奖励:积分点、爱意值点,解锁“中国文联合作权限”(可参与全国性打工者文化活动策划)。】
林晚星走到李娟的画作前,看着画中夕阳下忙碌的流水线工人,忽然想起陈雨在拍摄时说的一句话:“我们拍的不是电影,是无数个平凡人用热爱点亮的光。”她转头看向正在唱歌的王哥,看着台下脸上带着笑容的打工者,心中忽然明白,“新星导演计划”的真正意义,不是扶持出多少知名导演,而是用电影的力量,让那些被忽略的群体、被遗忘的梦想,得到关注与尊重。
“以前总觉得,电影的价值在于票房、在于奖项,”林晚星对身边的陈雨说,“但现在现,电影最大的价值,是能引社会的思考,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就像《城市之光》,它让更多人关注到打工者的精神需求,让更多打工者有勇气追求自己的热爱,这比任何票房都更有意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陈雨深有感触地点点头:“记得拍摄时,有位打工者跟我说,‘从来没想过我们的生活能被拍成电影’。现在,他们不仅能在电影里看到自己,还能在现实中拥有展示梦想的平台——这才是我们做这件事的终极意义。”
艺术展的角落里,几位来自苏州电子厂的女工正围着一幅画讨论。画的是电子厂车间的夜景,流水线的灯光像一条银色的河流,工人们的身影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角落里却藏着一抹小小的亮色——一张贴在机器上的写画。“这画的不就是我们车间吗?”一位女工指着画说,“我也喜欢在休息时画画,以前总觉得是瞎画,现在看了这个展览,我也想把我的画投稿过来。”
负责展览策划的工作人员立刻递上报名表:“我们的‘打工者艺术展’会长期征集作品,不管是画画、书法,还是手工制品,都可以投稿。后续我们还会把优秀作品汇编成画册,在全国的文化服务中心巡回展出。”女工们接过报名表,指尖轻轻摩挲着纸张,眼神里满是期待——这种“被看见”的机会,对她们而言,比任何奖励都珍贵。
林晚星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城市之光艺术计划”启动时的场景。当时团队在深圳某打工者社区建立第一个“艺术空间”,初期只有个人报名参加绘画班,其中就有李娟。如今,仅半年时间,全国o个“艺术空间”已累计吸引过ooo名打工者参与,不少人还组建了自己的艺术小组——电子厂的“流水线画社”、外卖员的“街头歌者联盟”、工地的“钢筋街舞团”,这些原本散落的“热爱”,因为电影和计划,渐渐汇聚成了照亮城市的“光”。
“解锁的新任务,其实是把‘偶然的温暖’变成‘长久的支持’。”林晚星在后续的项目筹备会上说。“全国打工者文化扶持项目”不再局限于“艺术培训”,而是要打造“一站式文化服务”——每个“文化服务中心”不仅配备绘画室、音乐室、舞蹈室,还会邀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定期授课,提供作品展览、版权保护等服务;针对有潜力的打工者创作者,还会对接文化机构,为他们提供职业展的机会。
“比如李娟,她的画作《流水线的夕阳》现在已经被某艺术机构收藏,我们正在帮她申请个人画展。”项目负责人说,“我们希望让‘热爱’不仅能成为‘精神出口’,还能成为‘职业选择’——当然,这不是强求,而是给那些有梦想的打工者,多一个选择的可能。”
“打工者影像计划”则更注重“让打工者自己声”。团队会为参与计划的打工者提供摄像机、剪辑软件等设备,以及基础的影像制作培训,让他们用镜头记录自己的生活、工作与梦想。“我们不会干预他们的创作方向,不管是记录流水线的日常,还是讲述与家人的故事,甚至是拍摄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都可以。”计划统筹张磊说,“之前有位外卖员拍摄了《我的一天:从清晨到深夜》,镜头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送餐路上的风雨、顾客的一句‘谢谢’、深夜回家时楼道的灯光,却在短视频平台获得了过oo万的播放量——这种‘真实的视角’,比专业团队拍摄的纪录片更有感染力。”
该计划还与国内多家视频平台合作,开设“打工者影像专区”,为优秀作品提供流量扶持与传播渠道。“我们希望让更多人通过打工者自己的镜头,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不是媒体报道里‘辛苦的符号’,而是有热爱、有梦想、有情感的‘普通人’。”林晚星说。
中国文联在得知项目计划后,主动提出合作意向,不仅会为“文化服务中心”提供政策支持,还会将“打工者影像计划”的优秀作品纳入“全国现实主义影像展”,让打工者的故事走进更广阔的舞台。“《城市之光》证明了,打工者群体的故事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中国文联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愿意与晚星娱乐合作,共同推动打工者文化的展,让更多平凡人的梦想被看见、被尊重。”
当天晚上,林晚星收到了李娟来的消息,附件里是一幅新画——画的是“文化服务中心”的绘画室,几位女工围坐在桌前画画,窗外的阳光洒在她们身上,画面温暖而明亮。消息里写着:“林总,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也能这么精彩。我现在每天都来画画,还带了三个工友一起,我们想组成‘女工画社’,以后一起创作,一起参展。”
林晚星看着画,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她回复道:“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你们自己的热爱与坚持。未来,会有更多人看到你们的画,听到你们的故事——你们才是真正的‘城市之光’。”
窗外的上海,夜色正浓,霓虹闪烁的高楼间,藏着无数个像李娟、王哥这样的打工者。他们或许仍在流水线上忙碌,或许还在街头奔波,或许正躲在出租屋里坚持自己的热爱。但林晚星知道,《城市之光》与后续的扶持项目,就像一束微光,虽然微弱,却能照亮那些被忽略的角落,让更多平凡的梦想,有机会在阳光下绽放。而她的生命,也在这一次次“传递温暖、守护梦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厚重、更有意义——这比任何“生命值”的数字,都更能诠释“逆天改命”的真正含义。
喜欢星光重启:爱意系统助我逆天改命请大家收藏:dududu星光重启:爱意系统助我逆天改命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
![我是首富的亲姑姑[年代文]+番外](/img/763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