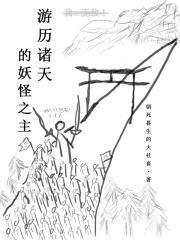91言情>快穿:气运男主集体罢工了 > 第61章 摄政王不走替嫁剧本04(第1页)
第61章 摄政王不走替嫁剧本04(第1页)
从晨露未曦到日影西斜,江清澜好好洗漱更衣,又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她特意吩咐陪嫁丫鬟留下整理嫁妆,不必跟随。
在下人的引领下,独自走向演武场。
微湿的梢还泛着淡淡水汽,胭脂色的骑装衬得肌肤莹白如雪,整个人神采奕奕。
申时已过了一大半。
暮色初临,演武场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霜,江清澜走进去时,萧景珩早已勒马而立。
一袭玄色窄袖劲装勾勒出挺拔的身形,腰间银纹蹀躞带在余晖中流转着冷光。
“王爷久等了?”
江清澜踩碎满地薄霜走近。初冬的风掠过她耳际碎,倒衬得人愈精神。
萧景珩斜倚在马鞍上,目光在她身上打了个转,觉得她这身很美,嘴上还是不饶人:“本王还以为,王妃又要玩失踪的戏码。”
“王爷这么惦记我呀?”
她停在马前,眼波流转,伸手就要去够缰绳。
“怕你摔了赖我的马。”他嘴上这么说,手却已经扶上她的腰。
谁知江清澜根本不待他托举,一个利落的翻身就上了马背。
缰绳轻抖间,那匹烈马竟乖顺地稳住了步伐,小跑出去几步。
初冬的黄昏风里带着微凉,萧景珩的目光却凝在她执缰的手上。
那纤细的手指收放缰绳的力道精准得不似闺阁女子。
“侯府的闺秀,骑术倒是了得。”他眸色微沉,语气里辨不出是赞赏还是试探。
江清澜勒马回身,梢在暮色中扬起:“我的外祖父,小时候教过我。”
原主的母亲江周氏,虽出身国公府嫡次女,却因性子过于绵软,终究没能承袭将门虎女的风骨。
“王爷不是要教我骑马么?怎么反倒是我在等您?”
萧景珩倏然轻笑,抬手示意亲卫。
另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被牵来时,他纵身上鞍的动作行云流水:
“既然王妃想比试,输了可别哭。”
暮色渐沉。
演武场上最后一缕霞光将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
江清澜放缓了马,胭脂色的衣袖被晚风轻轻拂动,与萧景珩玄色的衣袂偶尔相触又分开。
萧景珩侧目看她,现她眉目间的锋芒不知何时已柔和下来,正望着天边初现的星子出神。
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缰绳,让两匹马靠得更近了些。
“王爷的马很温顺。”
她忽然开口,手指轻抚过乌云驹的鬃毛。
“它平日不这样。”
萧景珩低声道,目光落在她抚马的手指上,“倒是第一次见它对外人这般亲近。”
江清澜忽然轻一声,抬手指向西苑一角:“王爷快看。”
最后一缕夕阳穿过演武场西侧的梅林,将嶙峋的枝桠映成耀眼的金红色。
几朵红梅在暮色中格外醒目,花瓣上还凝着未化的薄霜。这王府景色确实很美。
萧景珩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常年冷峻的眉宇不自觉地舒展。
他轻夹马腹,战马便乖顺地朝梅林踱去。
暮色中,两人勒马驻足,一同观赏梅林风景。
“这株朱砂梅是先帝所赐。”
他忽然开口,却看向某个梅树的树干上那明显是刀剑留下的刻痕,语气晦暗不明。
“赐下时,曾说:愿它岁岁常红。”
江清澜敏锐地察觉到他话中深意。
梅香清冽,可枝干上却有一道陈年剑痕,切口凌厉,似是与这风雅景致格格不入的旧伤。
远处传来急促脚步声,凌风跪地呈上密报。
萧景珩展信一瞥,眸色骤冷。
江清澜目光不经意掠过信笺,只见纸上墨迹略显生涩,笔画间带着不自然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