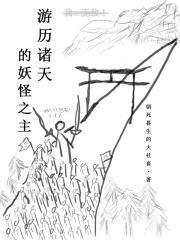91言情>奸臣洗白计划 > 第75章 红袖招 朱雀大街过满楼红袖招(第2页)
第75章 红袖招 朱雀大街过满楼红袖招(第2页)
苏锦绣指尖一顿,擡眸道:“怎麽了?”
“如今京中都在传呢!”琳琅压低声音,“那圣女本是要献上入宫的,可太後说她容貌太过妖媚,恐扰得後宫不宁,竟当场改了主意,把人赐给小侯爷做妾了!”
“当场赐作妾室?”苏锦绣攥紧帕子追问,“他纳下了?”
“这倒说不清,只知宫里是这麽传出来的。”琳琅摇了摇头。
苏锦绣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被圣恩留住,竟是故意躲着她。
分明是又存了什麽鬼胎,却连一句缘由都不肯与她说明,这般讳莫如深的模样,竟与往昔某些时刻如出一辙。
第三日,苏锦绣骑着枣糕,未等宫门下钥便已候在宫墙之外。
他凭功班师归来,没有连宿宫中三日的道理。想来今日必得出宫,她索性在此守株待兔,倒要当面问个明白。
枣糕在原地轻踏蹄子,尾鬃扫过地面,似是十分焦躁。
苏锦绣拢了拢外衫,目光定定落在宫门处,倒要瞧他这一回,如何能避而不见。
心底纵有两分怨愤,馀下八分却仍浸在期待里,缠缠绕绕,难分难解。
她心底明镜似的,只要他肯露面,哪怕只在近前站定,说一句“实在是公事难违”,那两分怨愤便会如融雪般消散,她亦能立刻将前几日的猜疑和等候的委屈,尽数抛在脑後。
就这般立在落日馀晖中候着,直至天边最後一抹霞光褪尽,直至秋夜的寒凉渐次漫来,也没等来想见的身影。
远处忽有车马声渐近,不是她盼的那辆。
那马车行至近前便停了,车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撩起,露出一副风流好皮相,竟是崔澄。
“呦,这是谁惹的风流债,竟教这等貌美的小娘子在此苦等?”
苏锦绣懒得与他周旋,勒转枣糕的缰绳便要掉头。身後却传来崔澄的唤声:“喂!别在这空等了,你要找的人,去了鸣玉坊。”
苏锦绣顿了顿,随後便策马向那绛烛摇光,麝馥袭人的地方去了。
此坊名唤鸣玉,却与醉春坊判若云泥。醉春坊多蓄清倌,坊中女子皆怀咏絮之才,守着“卖艺不卖身”的规矩,往来者亦多是品茗论诗的雅客。
可这鸣玉坊却大不相同,满庭皆是西域来的女子,多的是热辣奔放的胡姬,藏着些重金便能成交的皮肉交易。
此时恰逢华灯初上,是鸣玉坊最热闹的时候,笑语欢声缠作一团。
苏锦绣冒着脂粉气的风,举步跨进门去。
刚过门庭,便被个敷粉施朱的老鸨截住去路,那老鸨上下打量她一番:“哎哟,这小娘子看着面生得很,莫不是误闯了地方?”
苏锦绣懒得与她饶舌,只从袖中摸出三锭赤金,径直砸了过去,这一路上便畅通无阻。
她目不斜视地往里走,掠过满堂的衣香鬓影,一间间挨个儿看过去。
但凡有上前搭话的胡姬或侍者,都被苏锦绣一把推开,半分情面也不留。她步子迈得利落,心底却早已替他寻尽了缘由。
许是哪个混账下属不知轻重,仗着几分酒意硬拉他来这风月场应酬,他只是难拂同袍颜面。许是官家暗中授了密差,要他借这声色场所查探什麽隐秘,毕竟灯下黑处最易藏事。
就这样一遍遍自圆其说,眼底悄悄想要下雨,心里却偏要替他撑起一把伞。
直到最深处那间门帘半敞着,听见里头熟悉的笑声。
苏锦绣隔帘窥望,见里面三五男儿围坐,有一背影十分熟悉,正居上座,玄色衣袂衬得脊背挺括。
此间原是鸣玉坊里最大也最金贵的一间,里头陈设阔绰,两侧梨花木长案横陈,案上珍馐罗列,琼浆盈樽,如小型宴厅一般。
中庭架起露天莲台,四周银纱垂落,将台上光景笼得若隐若现。
台上立着三位眼眸如猫瞳般的胡姬,身着露肤的碧绿舞衣,腰间裙摆随着热辣舞步翻飞,足踝金钏沙沙作响,晃得人目眩神迷。
那熟悉背影身旁还依偎着个着雪色异服女子,正凑在他耳边低语,引得他低笑出声,竟无一人察觉她已一步步走近。
一坛从天而降的女儿红。
满座皆骇然变色,闻时钦霍然站起,旋过身来,想借着昏灯错影,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擅闯者。
苏锦绣擡眸望他,见他拭去满脸酒液,又眯眼打量,似在辨认她是谁。
她便这样静静等着,直到他豁然开朗,直到他的怒意如潮退般瞬时消弭,唯馀胸口剧烈起伏。
酒液自他的面颊滑落,顺着修长脖颈,浸透衣襟。
二人便在这昏晦灯影里默默对峙。
闻时钦擡手一止,那护卫便立刻噤声。
他转身离了衆人,避之不及一般,踱至不远处的软榻旁落座。
苏锦绣未发一语,亦步亦趋到他面前,明晃晃是要他给个交代。
此处灯影更昏沉,闻时钦始终垂着眼,不知是心虚躲闪,还是另有隐情,只缄默地坐着。
苏锦绣有的是耐心与他耗,就那样不卑不亢立在跟前,眸光沉静。
那边衆人勉强理清状况,却无一人敢上前劝和,这等牵涉私隐的僵局,谁也不愿触霉头。
唯有那雪衣圣女,趁着这僵局,悄悄提了裙摆,想悄步挪到闻时钦身侧。
恰在此时,闻时钦深吸一口气,终是擡眼要开口。苏锦绣却不给他半分言语的机会,扬手便扇了他一记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在寂静里格外刺耳,闻时钦被打得偏过头去,颊边瞬时泛起红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