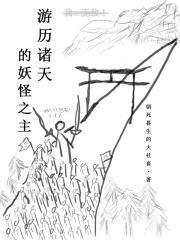91言情>综影视:卷王功德系统之女配救赎 > 第30章 父女对面(第1页)
第30章 父女对面(第1页)
这一夜,唐薇几乎未曾合眼。
窗外慈宁宫的更漏声滴答,每一滴都像是敲在她的心坎上。脑海中反复预演着次日与父亲陈邦直相见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白、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意外及应对。掌心因紧张而不断渗出冷汗,又被她一次次悄悄擦去。
天光微熹时,绘春带着两个宫女早早便来了。今日的衣裳比往日更加素净庄重,是一件藕荷色净面缎袍,只在衣襟处用银线绣了寥寥几枝忍冬纹,髻也梳得一丝不苟,簪了支素银簪并两朵白色绒花。这副打扮,既符合她“戴罪静修”的身份,又不会在面见父亲时过于失礼,拿捏得恰到好处。
“姑娘今日气色倒好些。”绘春一边为她整理衣襟,一边似是随意地说道,目光却细致地掠过她的眉眼。
唐薇垂下眼,低声道:“许是……许是想到能见父亲一面,心中……心中难免有些激动。”她适当地流露出些许期盼和不安,完美扮演着一个久困深宫、骤闻亲人消息的柔弱女子。
用过早膳,她便被引至慈宁宫一间位置相对偏僻,却依旧在太后势力范围内的偏殿等候。殿内陈设简单,香炉里燃着淡淡的檀香,空气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她端坐在绣墩上,双手交叠置于膝上,指尖冰凉。目光低垂,看着地面金砖的缝隙,努力调整呼吸,将所有的情绪压入心底最深处,只留下表面一层符合期待的、带着怯懦和渴望的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殿外终于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宫女们轻巧的步子,也不是太监急促的碎步,而是另一种——属于男子的、沉稳而略显滞重的脚步声,伴随着轻微的玉石叩击声(似乎是朝珠或佩玉)。
唐薇的心脏猛地一跳,几乎要跃出胸腔。她迅抬了一下眼,又立刻低下,双手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襟。
殿门被推开。
绘春的声音响起:“陈大人,请。姑娘已在殿内等候。”
一个穿着深色朝服、身形微胖、面容带着官场历练出的沉稳与些许疲惫的中年男子,迈步走了进来。正是陈邦直。他的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了殿中低头坐着的女儿身上,眼神复杂无比,有关切,有忧虑,有审视,更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痛心与焦急。
“奴才叩见……”陈邦直依照规矩,便要向这位虽是罪眷却仍有名分的侧福晋行礼。
“父亲!”唐薇仿佛再也抑制不住,猛地站起身,声音带着哭腔打断了他,却又像是想起宫规,硬生生停住脚步,只是红着眼圈,哽咽道:“父亲……不必多礼……女儿……女儿……”她语无伦次,泪水恰到好处地盈满眼眶,却强忍着不让其落下,将一个委屈又克制的女儿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陈邦直的动作顿住了,他看着女儿苍白清减的脸庞,那身素净得近乎寡淡的衣裳,还有那包裹着纱布的右手,眼中掠过实实在在的心疼。他快步上前,虚扶了一下,声音也带上了几分沙哑:“快坐下……你……你的手怎么了?在宫里……可还过得去?老佛爷她……”
一连串的问题,透着真切的焦急。
唐薇却在他靠近的瞬间,几不可查地微微向后缩了一下,仿佛惊惧,随即又强迫自己站定,低下头,用细若蚊蚋的声音道:“劳父亲挂心……女儿一切都好……手是不小心摔的……快好了……老佛爷慈悲为怀,对女儿极好……每日诵经抄经,心里也安稳多了……”
她句句都在说“好”,语气却带着难以掩饰的艰涩和勉强,尤其是提到“诵经抄经”时,那微微颤抖的声线,更像是一种无言的控诉和麻木的接受。
陈邦直是何等人物,官海沉浮多年,瞬间便听出了女儿的言外之意。他的脸色白了白,眼神更加复杂,痛心疾地低声道:“是为父无用……未能护你周全……才让你在此受这等苦楚……”
“父亲千万别这么说!”唐薇猛地抬头,眼中泪水终于滑落,却飞快地用袖子擦去,努力做出坚强的样子,“是女儿自己……当初年少无知,行了错事,合该受罚……能得老佛爷庇护,在此静思己过,已是天大的恩典……女儿如今只想安心赎罪,别无他求……”
她再次强调“赎罪”和“别无他求”,目光恳切地看着父亲,仿佛在哀求他不要再问,不要再提,以免惹祸上身。
陈邦直看着女儿这般情状,喉头滚动,似乎有千言万语,最终却只是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他注意到了女儿身后小几上那厚厚一叠抄写的经文,以及那明显是左手书写的、稚拙却极其工整的字迹。
他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了片刻,眼中闪过一抹深思,随即收敛,转而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巧的锦盒,递了过去,声音压得更低:“家中一切安好,你不必挂心。这是你母亲……替你求的平安符,望我儿……平安顺遂。”
锦盒很轻。唐薇双手接过,指尖接触到父亲微凉的手掌,能感觉到他几不可查地用力按了一下锦盒。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有东西!
唐薇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依旧是感激涕零:“多谢母亲……多谢父亲……”她将锦盒紧紧抱在怀里,如同抱着什么珍宝。
父女俩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话,句句不离“感恩”、“静养”、“赎罪”。陈邦直几次欲言又止,眼神瞥向殿外(绘春很可能就在附近),最终都化为了无奈的叮嘱。
时间很快过去。
殿外传来绘春轻轻的咳嗽声。
陈邦直神色一凛,立刻站起身,恢复了臣子的恭敬姿态:“时候不早,奴才不便久留,望……望姑娘保重身子,谨遵老佛爷教诲。”
唐薇也站起身,依依不舍,泪光盈盈:“父亲也要保重身体……旧疾……切勿再犯了……”她终于隐晦地提了一句“旧疾”,目光紧紧盯着父亲。
陈邦直身体几不可查地一震,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异色,随即垂下眼,含糊道:“劳姑娘记挂……老毛病了,无妨……无妨……”
他行礼告退,转身离去的那一刻,唐薇清晰地看到,他朝服的后背心处,已被汗水微微浸湿。
殿门缓缓合上,隔绝了父亲的身影。
唐薇独自站在原地,怀中抱着那个小小的锦盒,仿佛还能感受到父亲方才的紧张和那份无声传递的重量。
她缓缓坐回绣墩,没有立刻打开锦盒,而是先沉浸在一种复杂的情绪里——方才那场表演耗尽了心力,而父亲那句含糊的“无妨”,更是让她心头疑云密布。
旧疾是假?那他为何冒险递牌子进宫?只为确认她的安危?
旧疾是真?那他为何又说“无妨”?
还有这个锦盒……
她深吸一口气,确认殿外无人窥视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
里面果然并非什么平安符。锦盒底部,平平整整地放着一方素白的、绣着青竹的手帕。手帕本身并无异常,但当她拿起手帕时,却现下面压着一小卷极其轻薄、几乎透明的桑皮纸。
她的心跳骤然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