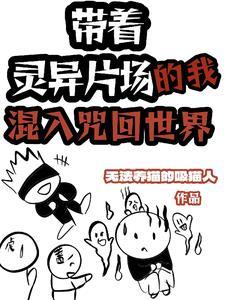91言情>一刀斩断旧时月+番外 > 第44章(第2页)
第44章(第2页)
连高台王座上的南向晚,一直平稳的气息,也几不可察地紊乱了一瞬。他搭在王座扶手上的手指,微微蜷缩,指甲抵住了冰冷的骨质。
在无数道或惊惧、或好奇、或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下,一道身影,缓缓自黑暗中踱步而出,踏入了幽冥鬼火映照的范围。
一身白衣,已然染尘,甚至能看到些许暗沉的血迹,却依旧不改其挺括。墨发依旧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着,几缕碎发垂落额前,遮住了部分眉眼。
正是黎时樾!
他竟然真的单枪匹马,踏入了这龙潭虎穴般的幽冥总坛!
与半年前相比,他清瘦了许多,脸颊微微凹陷,使得下颌线条更加锋利如刀。脸色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苍白,仿佛久不见日光。而最令人心惊的,是他那双眼睛。
曾经清冷如寒星,如今却如同两口枯寂了万年的深井,里面不再有波澜,不再有情绪,只有一片死寂的、深不见底的黑暗。唯有在那片黑暗的最深处,似乎跳跃着一点猩红的、近乎疯狂的星火。
他的腰间,空空如也。
那柄伴随他多年的“霜降”剑,并未佩戴。
他一步步走来,无视周围那无数道几乎要将他穿透的视线,目光自始至终,都牢牢锁定着高台王座之上,那个银发玄袍的身影。
那目光,复杂到了极致。有痛楚,有审视,有恍如隔世的陌生,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几乎要化为实质的确认与……贪婪?
南向晚迎着他的目光,心脏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一股混杂着恨意、快意、以及某种难以言喻酸楚的情绪,猛地冲上心头。
他强迫自己维持着魔尊的威严与冷漠,甚至刻意勾起一抹带着讥诮与恶意的笑容。
黎时樾在距离王座十丈之遥处停下脚步。
整个幽冥殿,落针可闻。
所有人都等待着,这位凶名在外的“血剑”,将会如何应对魔尊的羞辱。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黎时樾微微抬眸,看着王座上的南向晚,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沙哑,却清晰地传遍了死寂的大殿:
“我来了。”
折剑惊澜
“我来了。”
三个字,低沉沙哑,却如同惊雷,炸响在死寂的幽冥殿内。
黎时樾站在那里,白衣染尘,身形比记忆中清瘦了太多,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可他就那样站着,如同一柄收入破旧皮鞘、却依旧散发着无匹锋芒的古剑。那双曾经清冷如星的眸子,此刻只剩下枯寂的黑暗与深处一点猩红的疯狂,牢牢锁在王座之上。
南向晚的心脏,在那一瞬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骤然停跳了一拍。
他真的来了。
单枪匹马,踏入这龙潭虎穴,只为……赴他这充满羞辱的邀约。
无数念头在南向晚脑中电光火石般闪过,最终都被强行压下,化为王座之上,那魔尊冰冷的、带着讥诮与恶意的面具。
他微微调整了下坐姿,玄色袍袖拂过冰冷的白骨扶手,发出一声细微的摩擦声。他刻意放缓了语速,声音带着魔气浸润后的低沉与磁性,在这空旷的大殿中清晰地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