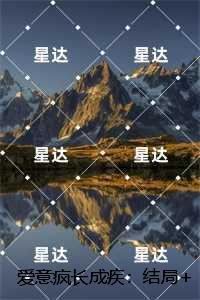91言情>杀过的白月光来找我了 > 第148章 樱笋时十二(第4页)
第148章 樱笋时十二(第4页)
沈如晚瞪了他一眼,可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趁着夜深人静,路边半点人影也没有,倾身倚在他肩头笑个不停,“长孙寒,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和我以前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无论她说多少次,他都蓦然从心底生出一股莫名隐秘的窃喜。
“是么?”他垂下头,不知何时停下了脚步,轻轻抚着她柔软细腻的发丝,声音低低的,在温存耐心下深埋着隐秘的诱引,像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你喜欢我什么样?“
沈如晚靠在他肩头,侧过身,埋在他颈窝里,声音贴着他肌骨血肉,从心口震颤到耳边,比黄钟大吕更振聋发聩,几乎蕴含着一种让人神摇意夺的力量,又那么轻描淡写,“我以前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一直以为长孙师兄孤高超凡,如星如月,不可触碰。“
长孙寒有点好笑,“那你还托邵元康引荐我?“
都如星如月不可触碰了,还找人引荐做什么?
沈如晚抬起头,半真半假地瞪他。
“那我总要留个念想,万一心想事成了呢?”她说着,又重新低下头埋在他颈窝里,“现在不就成真了吗?虽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她说着说着还叹口气。
长孙寒高高挑眉。
“怎么不一样了?”他似笑非笑,“沈师妹,你说说,到手了就不稀奇了,有这样的道理吗?“
沈如晚轻轻哼了一声。
她抬起头,额头贴着他下巴,微微向后仰了仰,目光落在他唇上。
目光分明无形无状,可他只觉得痒。
轻轻的,像浅淡的风,一点点拂过他唇瓣,痒到心底去,几乎穿心挠肺的痒意。
长孙寒没动。
他僵硬地立在那里,喉结很缓慢地滚动。
沈如晚很轻地笑了一声,他甚至还没明白她为什么笑。
“现在我知道了。”她轻轻说,笑意盈满每一声息,“长孙师况根本没那么克己自持,一点都经不起逗。“
长孙寒声音喑哑,“是么?”
沈如晚微微仰起头,目光和他相对,笑盈盈的,一点挑衅,“我看是。”
长孙寒忽而抬起手,五指扣在她颊边,微微用力。
他很微妙地叹了口气,嗓音低哑,可语调却放得很平缓,慢条斯理的,“沈师妹,我真的是经不起逗的,我是会当真的。”
沈如晚眼睫轻轻颤动着,偏偏还轻声笑,“那你怎么当真啊?我。。。。…”
长孙寒垂下头,将她声息都封缄在唇齿,贪婪吞咽在杂乱急促的呼吸间,就像是最狡猾的凶兽,蛰伏在无声无息的隐秘角落,骤然出没,露出最贪蛮无度的渴盼,无尽索求,永不止息。
这个吻和从前都不一样。
更蛮横,也更贪婪,那么肆无忌惮地拓深到遥远的疆界,陌生到让人战栗。
沈如晚想轻轻地推开他,可不知怎么的竟张开胳膊搂住他脖颈,拼了命地迎合,让这吻更深、更甜,几乎想融进他胸膛里去。
也许她从来没认识过她自己,她模模糊糊地想着,她快不认识自己了。
长孙寒低声问她,唇瓣贴着她的唇瓣,痒得让人发颤,“沈师妹,你说说,你是喜欢克己自持的,还是喜欢我现在这样的?“
沈如晚拒绝回答。
她仰起头,主动吻上他的唇,把这片刻欢愉推深到最遥远的边界之外、清醒与迷离之间,分不清醒醉碎。
长孙寒的低笑声咽在喉头。
他紧紧箍住她腰肢,细细吻过她唇瓣,理智早已被潮水淹没,深埋在无法触及的地方,所见之处,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惊涛骇浪。
夜深人静,唯有蝉鸣偶尔喧嚣,让人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了身处何处,要去往哪里,只有这一刻,更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不终结。
梢头鸟儿忽而扑棱起翅膀,惊起数鸟急飞,一番响动。
树下的人也被这声响惊动,仿佛终于从梦寐中惊醒了一般,慢慢地分开了些,仍然恋恋不舍地彼此凝望着,一眼都不能少。
“我。……”沈如晚声音轻轻的,她开口时全然没想过自己究竟要说什么,直到第一个字蹦出,她才忽而回过神来,意识到先前是如何意乱情迷地坠入那个吻里恋恋不忘,脸颊微红,仓促地说,“已经很晚了,我要回第九阁了,再晚就来不及服用那个破障丹了!“
长孙寒被她逗笑了。
“这么着急验证破障丹的功用?”他声音轻飘飘的,带着浅浅的笑意,“那你刚才怎么不推开我?“
沈如晚瞪他。
她向后退,试图离开他怀抱,可他却搂得更紧。
“别着急走。”长孙寒用了点力将她留在怀中,“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没说,听完再走。"
沈如晚微怔地看着他。
“什么话?”她问。
“我想说的是,”长孙寒笑了,轻声说,“明天见,师妹。”
明天见。
每一天。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爱意疯长成疾:结局+番外陆心宁谢司砚陆心宁谢司砚
- 见陆心宁未说出口的话。商量取消婚约的事。之后几天,陆心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