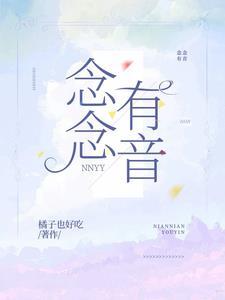91言情>同袍 > 第 9 章(第1页)
第 9 章(第1页)
第9章
京郊粮仓的红漆大门斑驳褪色,门环上的铜绿在秋日阳光里泛着冷光。谢清辞刚翻完第三本入库账册,指尖便在"糙米三千石"的记录上停住了——库房的地磅记录明明只有两千七百石,账面上却多了三百石的空额。
"又是虚账。"他将账册倒扣在案上,窗外传来晒谷场的扬鞭声,管粮仓的刘管事正呵斥着偷懒的役夫,皮鞭抽在谷堆上的脆响,像极了当年在东海听惯的渔网崩裂声。
萧砚之从粮囤後绕出来,靴底沾着麦糠,手里捏着把生虫的小米:"西仓第三囤的陈粮早就霉了,却还记在'新米入库'的账上。"他指了指墙角的老鼠洞,"这些虫蛀的粮,怕是连耗子都不爱吃,却要算成供给边军的军粮。"
话音未落,刘管事就掀帘进来,脸上堆着油光锃亮的笑:"两位大人辛苦了,小的备了些新米熬的粥。。。。。。"话没说完,就瞥见萧砚之手里的霉米,笑容僵成了面团。
“边军在北境啃冻窝头,你这里的好米却喂了虫?"谢清辞翻开朝廷的粮储章程,"新粮入库需晾晒三日,你这仓里的米,潮得能攥出水来,是想让将士们吃了闹肚子?"
刘管事的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这。。。。。。这是底下人偷懒。。。。。。"
"偷懒的怕是不止底下人。"萧砚之突然按住他按向腰间令牌的手,"上个月调往西北的粮草,账面是五千石,实际只发了三千五,剩下的去哪了?"他从袖中抖出张字条,是从刘管事卧房搜出的,上面"孝敬李御史"几个字墨迹未干。
当晚谢清辞核对粮价时,发现今年夏粮歉收,粮仓却按去年的低价报了购粮款,中间的差价足有白银千两。"李御史分管粮务,这差价怕是进了他的私库。"他在账册上画了个圈,"就像东海的密网,看似捞的是鱼虾,实则断的是生路——北境的军粮掺了沙土,灾民领的救济粮缺斤少两,都是从这些虚账里抠出来的。"
萧砚之正用布擦着剑上的锈迹,闻言擡眼:"明天去御史府。"剑刃映着他眼底的冷光,"粮仓的账能改,人心的贪念,得用规矩来磨。"
三日後,李御史被摘了乌纱帽,从他府中抄出的白银,恰好能补上粮仓的亏空。刘管事被杖责二十,发去晒谷场劳作,役夫们见他再不敢扬鞭,反倒主动教他如何扬谷筛糠。
谢清辞站在粮仓的高台上,看新到的军粮正被仔细晾晒,金黄的谷粒在阳光下像撒了一地碎金。萧砚之递来个刚蒸好的窝头,热气里混着麦香:"尝尝,用新米做的。"
咬下去时,谢清辞忽然想起东海的醉蟹,想起王伯说的"好好待它,总会留口饭吃"。他翻开账册,新的一页写着:京郊粮仓,亏空已补,新粮入仓。旁边萧砚之画了个圆滚滚的粮囤,顶上还站着只鸟。
那鸟儿被萧砚之画得歪头啄着谷粒,翅膀张得老大,倒像只刚从晒谷场扑棱起来的麻雀。谢清辞忍不住笑了,指尖在鸟喙上轻轻点了点:“你这画技,倒是比在东海画的鱼长进些。”
萧砚之挑眉,夺过账册翻到前页,指着那条尾巴翘上天的鱼:“这条鱼起码活灵活现,哪像你,记的账比粮仓的地磅还死板。”话虽如此,却伸手替他拂去肩头沾的麦糠——方才检查新粮时,谢清辞为了看谷粒饱满度,差点一头栽进粮堆里。
正说着,晒谷场上传来役夫们的笑闹声。刘管事正笨拙地扬着木鍁,金黄的谷壳随风扬起,落在他汗湿的背上。有个老役夫喊:“刘管事,扬得太高喽!谷粒都跟着飞啦!”刘管事红着脸应着,手上的动作却慢了些,倒真比先前像模像样了。
“知错能改,总不算太糟。”谢清辞望着那一幕,想起王伯儿子驾船出海时的笑,想起此刻谷粒在阳光下跳动的光,“这天下的账,有时也不全是冰冷的数字。”
萧砚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忽然从怀里摸出个东西,塞进他手里。是颗圆润的麦粒,饱满得能看出清晰的纹路。“方才在粮囤里捡的,”他声音放轻了些,“新麦,比去年的沉。”
谢清辞握紧麦粒,指尖传来谷物特有的坚实感。他低头翻开账册,在萧砚之画的粮囤旁,添了行小字:“仓廪实,民心安。”
风从粮仓的窗棂钻进来,带着晒透的麦香,吹动了账册的纸页。远处传来驿站的马蹄声,大概是又有急报送来了。萧砚之将剑系回腰间,声响利落:“下一站,该往哪去?”
谢清辞擡头,望向天边流云掠过的方向。西南的盐井,北境的军饷,江南的漕运……还有无数本等着算清的账。但他不急,指尖在账册上轻轻敲了敲,那里还留着东海的浪丶粮仓的麦,和两人并肩走过的痕迹。
“先去看看刚送来的急报吧,”他笑着起身,麦粒被仔细收进了账册的夹层里,“总有一处,等着我们去把账算明白。”
两人的身影走出粮仓大门时,阳光正落在红漆斑驳的门环上,铜绿在光里仿佛也暖了些。账册在谢清辞怀里轻轻起伏,像揣着一整个沉甸甸的人间。
急报是从江南漕运码头送来的,墨迹里还带着水汽。谢清辞展开信纸,眉头渐渐蹙起:“漕粮过淮水时,每船都要少三成,说是‘水耗’,可往年最多不过一成。”
萧砚之凑过来看,纸上画着漕船的简笔图,船底被圈了个红圈:“怕是船有问题。”他指尖点在红圈处,“故意在船底凿小洞,装模作样堵着,过闸时偷偷松开,粮袋泡了水,自然要‘耗’掉些——实则是把好粮换了出去。”
三日後,两人已站在淮水码头。漕船首尾相接,像条灰黑色的长龙伏在水面上。管漕运的周同知老远就带着人迎上来,脸上堆着笑:“两位大人怎麽亲自来了?这点水路小事,下官处置便是。”
谢清辞没接话,径直走向最近的漕船。船工正往岸上搬粮袋,有袋糙米破了口,滚出来的米粒半湿半干,带着股霉味。“这就是你说的‘水耗’?”他弯腰捡起粒米,捏碎了,里面是干的,“外面湿,内里干,倒像是故意泡的。”
周同知的脸僵了僵,刚要辩解,萧砚之已纵身跳上船顶,扯开舱板往里看。“这里藏着的,怕是不止水耗。”他扬声唤道,“谢兄来看看。”
舱底果然另有乾坤——暗格里堆着的不是漕粮,而是白花花的盐砖,砖上还印着“恒通号”的旧标记。谢清辞心头一沉:“漕运私盐,这是掉脑袋的罪。”
周同知腿一软,瘫坐在码头上。原来他勾结了恒通号的馀党,借着漕运之便私运盐砖,怕被查问,就想出“水耗”的名目掩人耳目,被克扣的漕粮,早被换成银子分了。
傍晚收押人犯时,码头上的船工围了过来,领头的老船工捧着本账簿,红着眼眶道:“大人,这是我们记的账,每船少了多少粮,都在上面。家里婆娘孩子等着漕粮下锅,我们不敢说,只能偷偷记着。”
谢清辞接过账簿,纸页粗糙,字迹却工整,每笔都记着日期和船号。他忽然想起东海的纳税册丶粮仓的地磅记录,原来这人间的账,从不是只有官府的册子才算数。
当晚在码头驿站歇脚,谢清辞对着灯火核账,萧砚之在旁磨墨。漕粮的亏空丶私盐的数量丶牵连的官员……一笔笔算下来,纸上的字迹渐渐铺满了月光。
“你说,这账什麽时候是个头?”谢清辞揉了揉酸胀的手腕,窗外的淮水声哗哗作响,像在数着没算清的数目。
萧砚之放下墨锭,从行囊里翻出个油纸包,打开是两个麦饼,还带着馀温:“刚在码头买的,加了新磨的芝麻。”他递过去一个,“账是算不完的,但算一笔,就少一笔糊涂账。”
谢清辞咬了口麦饼,芝麻的香混着麦香漫开来。他低头在账册新的一页写下:“淮水漕运,私盐被查,亏粮追还。”旁边,萧砚之画了艘歪歪扭扭的漕船,船帆上画了个大大的对勾。
“下一站,该去北境了。”谢清辞将麦饼的碎屑拍掉,指尖在账册上北境的位置敲了敲,“军饷拖欠的事,总得给戍边的将士们一个交代。”
萧砚之望着窗外渐沉的暮色,淮水的浪声里混进了归鸟的啼鸣:“听说北境刚下过雪,粮草怕是更紧了。”他起身将剑鞘上的水汽擦干,“早一日到,或许就能少些冻饿。”
三日後,两人换上了厚实的棉袍,踏上北境的土地时,脚边的积雪没到了脚踝。守关的校尉听闻他们来查军饷,红着眼圈把账本递过来:“大人您看,去年冬天的寒衣,到现在还没补齐。将士们握着冻裂的枪杆守城,有的兵卒,连顿热乎的粗粮都吃不上。”
谢清辞翻开账本,军饷的拨发记录停停断断,最近的一笔,还是三个月前的。而户部的回文写着“粮饷已足额拨付”,墨迹崭新得刺眼。“银子去哪了?”他指尖划过“足额”二字,指节泛白。
萧砚之在营房转了一圈,回来时手里攥着块冻硬的窝头,上面还沾着冰碴:“夥夫说,这是今天的早饭。”他看向校尉,“负责押送军饷的官员,是谁?”
“是兵部郎中张显,”校尉声音发颤,“每次来都带着好几车‘私货’,说是给将军的,可将军从来没收过。上个月他来,还说军饷被雪困住了,要等开春才能到。”
当晚,谢清辞在灯下核对转运记录,发现张显押送的军饷车队,每次都要在中途的“云来客栈”停留半日。“这客栈,怕是个幌子。”他在纸上画了个圈,“明日去看看。”
云来客栈藏在山坳里,看着不起眼,後院却停着三辆马车,车帘掀开,里面竟是绫罗绸缎和几箱烈酒。萧砚之揪住掌柜盘问,对方起初嘴硬,直到被搜出账本——上面记着张显每次“寄存”的物品,折算成银子,恰好与拖欠的军饷对得上。
“他把军饷换成了货物,运去关外倒卖。”谢清辞将账本拍在桌上,声音冷得像屋外的雪,“将士们在寒风里守城,他却用救命钱中饱私囊。”
张显被押来时,还在喊“我是兵部官员,你们敢动我?”直到萧砚之将那些冻硬的窝头扔到他面前:“这些,够你认识认识边关的滋味吗?”
张显霎时面如死灰。原来他勾结客栈掌柜,将军饷换成紧俏货物走私,再把赚来的银子存入私库,只把少许粗粮运到军营,谎称粮饷被耽误。
半月後,朝廷的补发军饷和寒衣送到了边关。谢清辞站在城楼上,看将士们领到新棉袍时红了的眼眶,看夥房飘出的炊烟里混着肉香,忽然觉得北境的风都暖了些。
萧砚之递来个热乎乎的羊肉汤饼,蒸汽模糊了两人的眉眼:“尝尝,夥夫刚做的,放了胡椒,驱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