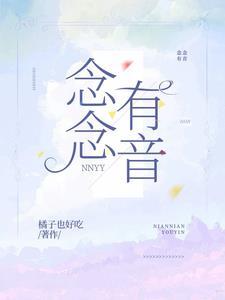91言情>同袍 > 第 9 章(第2页)
第 9 章(第2页)
谢清辞咬了一口,滚烫的汤汁流进喉咙,暖得人眼眶发热。他翻开账册,新的一页写着:“北境军饷,贪墨已追,寒衣到位。”旁边,萧砚之画了个披甲的士兵,手里举着个汤饼,饼上还冒着热气。
“西南的盐井,该去看看了。”谢清辞咽下最後一口汤饼,指腹摩挲着账册上“盐”字的刻痕——那是上次看急报时,无意识用指甲划下的印子。
萧砚之正用布擦拭剑上的霜花,北境的寒气总往金属缝里钻。“听说那里的盐价,比三年前翻了四倍。”他擡眼时,睫毛上还沾着雪粒,“土司说盐井减産,可百姓说,井里的卤水天天往外冒。”
半月後,两人走进西南的山坳时,空气里飘着股咸涩味。盐井旁的晒盐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老妪蹲在石臼前,用粗盐块捣着碎末,石臼边缘都被磨得发亮。“大人买盐吗?”一个老妪擡头,满脸皱纹里积着盐粒,“要不是家里娃娃咳得直喘,这点救命盐,说啥也不卖。”
谢清辞刚要问价,就见远处来了队骑马的兵卒,腰上挂着“盐务司”的牌子,为首的正是土司的侄子阿吉。“这盐场早就被土司大人收了,你们敢私下卖盐?”阿吉挥着鞭子,将石臼里的盐末扫进泥里,“再敢私售,打断你们的腿!”
老妪们哭着求饶,谢清辞上前一步:“朝廷规定,官盐定价每斤十文,你们卖多少?”
阿吉翻了个白眼:“土司大人说多少就是多少,现在一斤要五十文,嫌贵?嫌贵就别吃!”他勒马时,马鞍上的银饰晃得人眼晕,“去年大旱,朝廷拨的盐井赈灾款,够你们吃三年,可你们见过吗?”
这话让谢清辞心头一震。他翻出随身携带的户部文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拨银五千两,赈西南盐荒”。
当晚借住在山民家,屋梁上挂着串干瘪的盐巴,像串发白的骨头。山民大叔叹着气说:“盐井早被土司霸了,他把好盐运去关外换银子,给我们的都是带土的碎盐。去年的赈灾款?别说见了,提一句都要被打。”
萧砚之夜里去盐井探查,回来时靴底沾着盐卤,手里拎着个陶罐,里面盛着半罐雪白的精盐。“井里的卤水足得很,”他指着罐底的盐粒,“这是刚煮出来的,比官盐还纯。他们故意只开一口井,逼着百姓买高价盐。”
第二日,谢清辞带着文书去见土司,对方却装聋作哑:“盐井减産是天意,大人总不能跟老天爷讲道理。”
正争执间,晒盐场突然涌来百十个山民,手里举着带土的碎盐,跪在地上喊:“大人看看这盐!我们吃着带沙的盐,土司却用雪白的好盐换珠宝,连娃娃的救命盐都抢啊!”
阿吉见状,拔剑就要砍,却被萧砚之的剑架住了脖子。“朝廷的银子,百姓的盐,你们都敢吞?”萧砚之的剑刃上还凝着霜,“去年山民李大叔的儿子,就是因为没盐吃,咳血病死的,这事你敢不认?”
阿吉脸色煞白,土司却突然瘫在椅子上——他方才偷偷看了谢清辞手里的文书,上面盖着户部的朱红大印,字字都指着他贪墨赈灾款丶垄断盐井的罪证。
半月後,土司被押解进京,阿吉等人被杖责流放。朝廷派来的新盐官重新开了三口盐井,晒盐场上又铺满了雪白的盐粒,山民们背着盐袋时,脸上的笑容比盐粒还亮。
离开那日,老妪塞给谢清辞个布包,里面是几块压得紧实的盐巴。“这是新晒的好盐,大人带在路上,腌肉不腐。”她指着晒盐场,“你看这盐,就像人心,藏不住好坏,晒出来,亮堂堂的。”
谢清辞翻开账册,新的一页写着:“西南盐井,垄断已破,盐价归正。”旁边,萧砚之画了口冒着热气的盐井,井边画了个小人,正举着盐罐笑。
谢清辞摸了摸账册夹层,那颗麦粒还在,东海的浪丶粮仓的麦丶淮水的船丶北境的雪丶西南的盐,都在纸页间沉淀。他忽然笑了:“听说江南的茶税,近来也有些糊涂账。”
江南的茶山浸在春雨里,新抽的茶芽裹着水珠,绿得能掐出汁来。谢清辞站在山腰的茶寮外,看着茶农们把刚采的嫩芽倒进竹筐,筐沿却挂着层细网——网眼比东海的密网还小,刚好漏过最嫩的芽尖。
“这网是做什麽的?”他问旁边的老茶农。
老茶农往山下瞥了眼,压低声音:“税吏说,十斤鲜叶算一斤茶税,可他们用这网筛一遍,能筛掉两斤嫩芽。剩下的粗叶拿去报税,嫩芽就被他们私吞了。”
正说着,山道上传来铜铃响,几个穿着“税”字袍服的人扛着竹篓走来,为首的是江南茶税司的主簿赵三。“王老汉,今日的茶芽呢?”赵三踢了踢竹筐,“怎麽就这点?昨儿恒通号的少东家还来催,说要新茶待客。”
王老汉脸涨得通红:“嫩芽都被你们筛走了,剩下的炒不出好茶啊!”
赵三冷笑一声,指挥手下往筐里撒网:“朝廷的规矩,按筛後斤两算税,你当我乐意筛?”网眼晃过,细碎的芽尖簌簌落下,他弯腰把漏在地上的嫩芽扫进自己的篓里,“这些是‘损耗’,归公。”
谢清辞上前一步,指尖捏起片被筛落的芽尖:“朝廷税律,茶税按实际采制斤两征收,何时出过‘筛网’的规矩?”
赵三认出他身上的官服,却依旧嘴硬:“这是本地的‘土规’,大人远来,怕是不知江南的茶情。”他拍了拍篓里的嫩芽,“这些‘损耗’,是要上缴给府衙的,可不是私吞。”
当晚在茶农家住下,屋梁上挂着去年的陈茶,叶片发黄。茶农的儿子捧着本磨破的账本,上面记着每月被筛走的芽尖数量:“这些嫩芽能卖十倍的价钱,税吏们每月私吞的,比我们全家一年的嚼用还多。”
萧砚之夜里去了趟税司库房,回来时袖中沾着茶香,手里捏着张单子——上面记着“恒通号”每月从税司领走的“损耗”,数量竟比茶农们实际缴纳的茶税还多。“赵三说的‘归公’,怕是归了恒通号。”他将单子拍在桌上,“去年江南茶税歉收,户部却收到了超额的税银,原来是用这种法子凑的。”
第二日,谢清辞带着茶农们的账本去见知府。赵三闻讯赶来,身後跟着恒通号的少东家,正是当初东海被查封时漏网的分支子弟。“大人别听刁民胡说,”少东家摇着折扇,“这些茶农偷漏税,我们帮着税司核查,反倒被污蔑。”
话音未落,山上传来茶农的喊声。数百个茶农举着筛网和被筛落的嫩芽,跪在知府衙门前:“请大人看看!这就是他们说的‘损耗’!再这麽筛下去,我们连茶苗都要刨了种杂粮!”
赵三脸色骤变,刚要喝令驱赶,萧砚之已挡在茶农身前:“恒通号去年在东海犯的事还没清算,竟敢在江南重操旧业?”他指着少东家,“你父亲因密网捕鱼被抄家,你倒学了新花样,用密网筛茶税。”
少东家手里的折扇“啪”地掉在地上。原来他借着家族残馀势力,勾结赵三篡改税目,用筛网截留嫩芽贩卖,再将粗叶报作足额茶税,既赚了私利,又虚报了政绩。
半月後,赵三被革职查办,恒通号在江南的産业被尽数查封。新到的税吏带来了标准量具,茶农们捧着未被筛过的嫩芽过秤,筐里的绿芽堆得像小山。
离开茶山那日,王老汉用新茶泡了壶碧螺春,茶汤里浮着细小的毫毛,香得能染透衣裳。“这才是正经的春茶,”他给谢清辞续了杯,“大人瞧,这茶跟人心一样,掺不得假,一泡就显出来了。”
谢清辞翻开账册,新的一页写着:“江南茶税,苛政已除,芽归其主。”旁边,萧砚之画了株茶树,枝桠上挂着片叶子,叶尖还点着个小小的嫩芽,像颗刚冒头的星。
谢清辞摸了摸账册夹层,那颗麦粒丶那撮盐巴丶这片茶叶,都在里面安稳地躺着。他笑了笑,指尖指向西北:“听说那里的马场,草料账也有些不清不楚。”
马蹄踏过带露的青草,把茶香留在了身後。账册在行囊里轻轻翻动,东海的浪丶粮仓的麦丶淮水的船丶北境的雪丶西南的盐丶江南的茶……一页页记下去,像把人间的褶皱,慢慢熨成了平展的模样。路还长,但只要两人并肩走着,再细碎的账,也能一笔一笔,算成清明的日子。
暮春时节,谢清辞和萧砚之回到了京城。他们没先回官署,反倒绕去了城郊的市集。
刚走到街口,就见个卖糖画的老汉正往模子里浇糖稀,熬得透亮的糖汁在石板上凝成条鱼,尾巴翘得老高。谢清辞忽然笑了,碰了碰萧砚之的胳膊:“比你画的那条像样些。”
萧砚之挑眉,却没反驳,只指着不远处的粮摊——新麦刚下来,布袋上印着“京郊粮仓”的戳记,买粮的妇人正用手掂着分量,脸上带着笑。“看来刘管事把晒谷场的活计学扎实了。”他说。
两人沿街慢慢走,听见茶馆里的说书人正讲“东海密网案”,说有两位大人微服查访,愣是把户部侍郎的商号掀了个底朝天。邻座的茶客拍着桌子喊:“不止呢!听说北境的军饷丶西南的盐井,都是这两位大人理顺的!”
谢清辞刚要低头,却被个穿粗布衫的年轻人拦住。是王伯的儿子,背着半篓海货,说是来京城送新晒的鱼干。“我爹让我给大人带句话,”年轻人挠着头笑,“今年海货多,渔民们凑钱修了新码头,就等大人有空回去看看。”
正说着,街角传来熟悉的吆喝声。是江南茶山的王老汉,挑着两筐新茶,身边跟着个茶农小夥,正给路人分茶样。“谢大人!萧大人!”老汉眼睛亮得很,“这茶在京城卖得好,我们村盖了新学堂,娃子们都能念书了!”
萧砚之接过递来的茶包,茶香混着街面的烟火气,竟比在茶山时更醇厚些。他忽然想起什麽,从袖中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颗饱满的麦粒丶撮雪白的盐丶片干茶芽,还有片压平的海藻。
“账册记不下的,就用这些替吧。”他把布包塞进谢清辞手里,指尖触到对方掌心的薄茧——那是常年翻账册丶握笔杆磨出来的。
谢清辞没说话,只是握紧了布包。风从市集穿过去,吹起他袖口的褶皱,里面露出半截账册的边角,最新的那页没写新的去处,只画了个小小的圆圈,像枚印章,又像个圆满的句号。
暮色漫上来时,他们并肩往回走。街边的灯笼次第亮了,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青石板上,像从来就没分开过。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笃笃,笃笃,敲在渐沉的暮色里,也敲在那些被算清的账丶被抚平的褶皱里。
这天下的账哪有算完的时候?但此刻晚风正好,人间安稳,倒不如先歇脚,看看眼前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