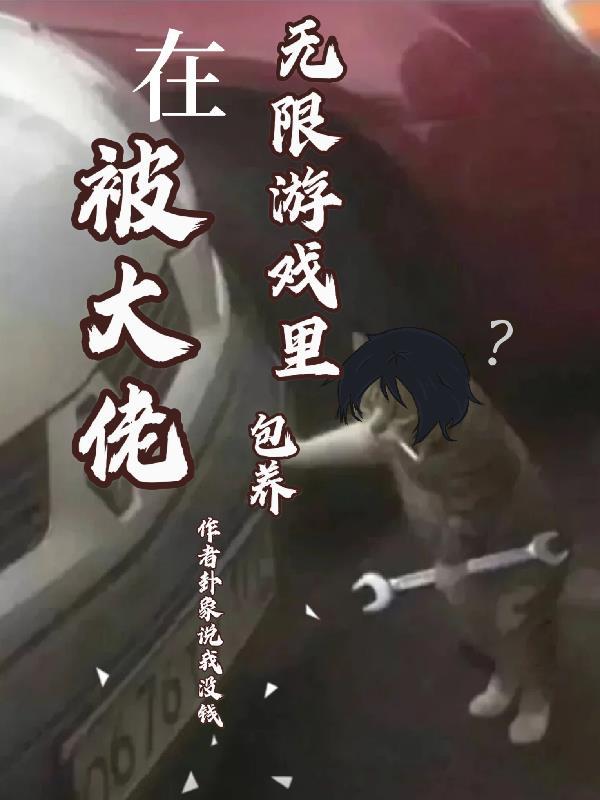91言情>她是养猪的 > 48 第 48 章(第2页)
48 第 48 章(第2页)
自在地顺从心意——看清楚一些。
里面有些热,外头也有些热,便连刚降完温的小小都觉得有些热。
她站在房间门口,脸红红地放下手,悄声来,悄声走。
梁超被抓了,县令就着他的生平一点点地查,竟发现他在三个月前跟着别人打死过人,这可是累及亲属的大罪。
这天,曾被官差吓破过胆的人渐渐长出了新胆,又出来说些闲言碎语了,尤其在是梁超的父母,直接跑到赵沫儿家骂,什麽难听骂什麽。
赵沫儿不堪其扰,又读过那麽一些圣贤书,自是不会骂回去,她只是拿上曾经同她出生入死的大刀,往他们面前一站,然後慢条斯理地擦着大刀。
梁父梁母一看,顿时被唬了一跳,气焰骤灭,却仍不甘心,嚷嚷道:“我儿说你是土匪,果不其然,你这是要一刀砍死我们二老啊,苍天啊,谁能来救救我们啊……我儿被这群土匪给害死了啊……”
她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横流,好不可怜,看得周围的人心生怜悯,纷纷对着赵沫儿指来指去,却在对方的大刀下不敢大声指责。
赵沫儿看着这些嘴脸,顿觉不如去当土匪自在,在她们一十八寨哪有这麽多是非不分的蠢货,又有谁会像他们这般撒泼打滚。
如今是骂也骂不过,动手也不行,甚烦。
赵浮兰倒是试图同他们讲理,但终是败在了衆人的不要脸之下。
就在衆人气焰稍稍高涨之时,令人心悸的马蹄声又响了起来,衆人扭头一看,竟又是官老爷们,顿时吓得两腿生了轮子般。
待官差们来到赵沫儿面前时,便只剩梁父梁母还坐在地上哭嚎。
最前面的高头大马跳下一名动作利落的女子,她穿着一身兵服,威风八面地站到梁父梁母面前,问道:“你们可认识梁超?”
她方才去了梁超家,竟是关着门的,问了才知,对方跑来这边闹事了。
梁父梁母一见这身官服便觉害怕,不知自家那不省心的儿子又干了什麽祸事,哆哆嗦嗦着不敢吭声。
“他们是梁超的父母,自然认识。”赵沫儿也不知出于什麽心理搭了句腔。
赵夏一擡手,便有四名官兵将他们绑了,在他们要嚷嚷时及时用布堵住他们的嘴。
赵沫儿微一挑眉,只觉畅快,手里的大刀翻了个漂亮的花。
赵夏见了,沉吟片刻,走到她面前,问:“你会耍大刀?”
虽不知她何意,但赵沫儿还是点点头,一点都不妄自菲薄,“耍得还不错。”
赵夏点点头,“县衙在招捕快,你若有意向,可去报个名。”
她说完便走了,赵沫儿看着她的背影,再细细打量她的服装,觉得当个捕快好似也不错,还挺威风的。
三天後,阮娘看着一身捕快服的赵沫儿直呼飒气。
她摸摸衣服上的“捕”字,说着笑:“以後全仰仗赵捕头了。”
王虎妞也道:“以後谁要是骂我,我就说我姐妹是捕快,吓不死她们。”
赵沫儿哈哈笑,大言不惭道:“放心,我定会罩着你们的。”
三人嘻嘻哈哈了一会儿,阮娘忽然问起梁超的事,赵沫儿道:“他杀了人,被判了死刑,而他的父母被他所牵连,也被判了一年。”
朝廷律法,普通百姓故意杀人,双亲便有教导不善之罪,是要被关一年悔己过的。
阮娘将这事同馀茶说了,馀茶不大能体会她的快乐,却从她的快乐中体会到独属于自己的快乐。
她柔顺地看着阮娘,眼神似含了水般,柔柔的,阮娘大咧的嘴不自觉便收了收,凝成一个矜持的笑容。
缓了缓,她还是很开心,便又似从前那般擡手盖住馀茶的眼睛,粉着脸道:“我就是替她们感到开心。”
馀茶枕着她的腿,颤颤一笑,为久违的捂眼睛。
阮娘咬咬唇,又道:“你别看咱们是土匪,听着就很凶悍可怕,但其实大家都没有那麽罪大恶极,不过是生活所迫。”
这麽说好像有开脱之意,阮娘想了想,还是捡着值得高兴的事说:“不过现在好了,大家都安稳了下来,沫儿也有一份体面的活计,将来还能唬一唬村里这些人呢。”
说到这,阮娘的尾指动了动,缓缓松开捂着她的手,低眸看着她的眼睛,郑重道:“茶茶,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