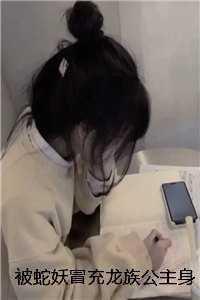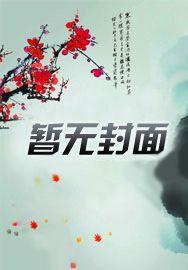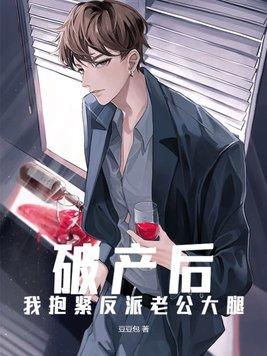91言情>六零小中医:开局救了个老太太 > 第116章 复诊调方燃希望双胎惊喜暖心间(第1页)
第116章 复诊调方燃希望双胎惊喜暖心间(第1页)
刘会英看着陈墨,眼里满是感激——半个月前,她还被“癌症”的诊断压得喘不过气,连饭都咽不下,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可现在,不仅能吃下半碗饭,身上还有了力气,甚至能帮家里洗衣服。这种从“绝望”到“有希望”的转变,让她觉得像做梦一样。
“大夫,真是谢谢您!要是没您开的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刘会英声音带着哽咽,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激动得说不出话。
陈墨笑着摆摆手,示意她放松:“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来,我再给你把把脉,看看恢复情况,调整一下药方。”
刘会英连忙伸出手,放在脉枕上。陈墨指尖搭上去,仔细感受着脉象的变化——比起上次,脉象明显有力了许多,沉细的感觉减轻了,涩脉也淡了不少,脾胃脉的搏动也更清晰了。这说明之前的药方起了作用,气血在慢慢恢复,瘀血也在消散。
“恢复得不错。”陈墨收回手,拿起笔,在纸上写新的药方,“之前的药方里,黄芪和山药的用量可以减一点,再加一味鸡内金,帮你消食化积。这个方子你连着喝五天,停两天,再喝五天,就先不用喝了。一个月以后再来复诊,记得把日子算清楚,别错过了。”
“您放心!日子我肯定记牢!”没等刘会英开口,她丈夫就迫不及待地保证,眼里满是激动,“这半个月来,我媳妇一天都没断过药,每天什么时候煎、什么时候喝,我都盯着呢!”
陈墨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里也暖暖的。他其实很想告诉这两口子,胃贲门癌在当下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根治,现在的治疗只能延长生存期、减轻痛苦。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没必要泼冷水,对癌症患者来说,“希望”有时候比药物更重要。让他们觉得有治好的可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反而对病情控制更有利。
“那就好。”陈墨把药方递给刘会英,又叮嘱,“这期间还是要注意饮食,多吃粥、烂面条这些软乎的,别吃硬的、凉的,也别生气——情绪对病情影响很大。”
“知道了大夫!我们都记住了!”刘会英两口子连连点头,小心翼翼地把药方叠好,放进布包里。这次离开时,他们的背影比上次挺拔了许多,脚步也轻快了,走到诊室门口,还特意回头对陈墨鞠了一躬:“谢谢您,陈大夫!”
陈墨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满是感慨——对病人来说,能活着、能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他正出神,突然瞥见诊室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大院里的阎埠贵,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一个布包,正冲着他点头微笑。
陈墨有点好奇——阎埠贵是小学老师,平时在大院里出了名的“抠搜”,连买根冰棍都要跟小贩讨价还价,怎么会突然来医院找他?他站起身,笑着招呼:“三大爷,您怎么来了?快进来坐。”
阎埠贵却站在门口,摆了摆手,脸上带着几分不好意思:“小陈,我就不进去了,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就走,不耽误你看病人。”
陈墨见他坚持,便走出诊室。阎埠贵拉着他往走廊旁边挪了挪,避开过往的病人,然后搓了搓手,眼神有点闪躲,小声说:“是这么回事,小陈——我想给家里买个收音机,现在买东西不是要工业券嘛,我那儿还差几张,想问问你这儿方便不方便,能不能借我几张?”
陈墨愣了一下,心里暗自嘀咕——没看出来啊,大院里最抠的三大爷,竟然是第一个想买收音机的!他还以为阎埠贵就算添置大件,也会先买自行车,毕竟有了自行车,他周末去郊区钓鱼也方便,没想到竟然是收音机。
他故意打趣:“三大爷,您可以啊!这都准备买收音机了,是想听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阎埠贵被说中了心思,嘿嘿笑了两声,有点得意:“可不是嘛!咱老百姓也得跟紧形势,听听新闻,知道国家政策,不然跟人聊天都没话题。再说了,家里有个收音机,孩子们也能听听评书,省得总出去疯跑。”
“您想借几张?收音机票您都有了?”陈墨问道——现在买收音机不仅要工业券,还得有专门的“收音机票”,不是有钱有券就能买的。
“三张就够!”阎埠贵伸出三根手指,语气急切,“我问过供销社了,一台收音机三十多块,需要两张工业券?不对,等一下,我再想想……”他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又改口,“哦对,二十块钱一张工业券,三十多块需要两张?不对,不足二十按二十算,三十多块应该是两张?不对,我再问问……”
陈墨忍不住笑了——阎埠贵这“抠搜”的本性又暴露了,连工业券的数量都要反复算计。他摆摆手:“三大爷,您别算了,收音机一般需要两张工业券,不过有的牌子可能需要三张。您要借三张,我这儿有,您明天过来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真的?那太谢谢了!”阎埠贵眼睛一亮,脸上的不好意思瞬间消失,语气也激动起来,“收音机票我已经拿到了,是从我们校长那儿要的——他亲戚在供销社,正好有多余的票,我跟他磨了好几天才给我。”
“行,那您明天上午过来,我给您准备好。”陈墨爽快地答应了——阎埠贵虽然抠,但人品没问题,借了东西肯定会还,而且只是几张工业券,他家也不缺。
“哎,好!太谢谢你了小陈!”阎埠贵激动得脸都有点红,又搓了搓手,“那我不耽误你了,我还得去学校上课,明天再过来找你。”说完,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脚步都比平时快了不少,显然是盼着早点把收音机买回家。
陈墨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笑了——再抠的人,遇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会变得大方。他回到诊室,刚坐下,王洁就进来了:“陈医生,刚才那个阎大爷是您家邻居?看着挺和蔼的。”
“是啊,住一个大院的,是小学老师,人挺好的,就是平时有点节省。”陈墨笑着说,“没想到他会先买收音机,我还以为他会先买自行车呢。”
王洁也笑了:“收音机现在可是稀罕物,我们家也想买,就是缺工业券和票,只能再等等。”
转眼到了中午,陈墨去中药房找丁秋楠,一起去食堂吃饭。丁秋楠刚坐下,就笑着说:“墨哥,跟你说个事——早上秦淮茹来找我了,想借五张工业券。”
陈墨愣了一下,有点意外:“哦?她借工业券干嘛?也是想买收音机?”
“不是,是想买缝纫机。”丁秋楠舀了一勺粥,慢慢喝着,“她说她婆婆贾大妈想买,说是有了缝纫机,能找居委会接点缝补的活,贴补家用。秦淮茹还说,一大爷帮她找了一张缝纫机票,就差工业券了。”
陈墨点点头——贾大妈平时看着有点强势,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觉悟。贾家靠着贾东旭的抚恤金过日子,虽然饿不着,但也不宽裕,要是能接点缝补的活,确实能改善生活。他想了想,说道:“你要是想借,就借给她吧,不过估计她一时半会还不上——贾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工资不高,工业券攒得慢。”
丁秋楠放下勺子,认真地想了想:“没关系,她们家确实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再说了,都是邻居,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陈墨看着她温柔的样子,心里暖暖的——丁秋楠总是这么善良,不管对谁都很包容。他突然想起阎埠贵的事,笑着说:“对了,早上三大爷也来找我了,想借三张工业券买收音机,我答应他明天给他。”
“啊?这么巧?”丁秋楠眼睛瞪得圆圆的,有点惊讶,“他们怎么会同一天来借工业券?不会是商量好的吧?”
陈墨耸了耸肩,有点无奈:“谁知道呢。不过咱们家工业券够,能帮就帮。但也得说好,要是以后有人贪得无厌,总来借,我可不会惯着。”
“哪能呢,都是邻居,怎么会总来借。”丁秋楠笑着说,给陈墨夹了一块青菜,“快吃吧,一会饭该凉了。下午你还要去保健组值班,别耽误了。”
吃完饭,陈墨把丁秋楠带回自己的诊室,让她躺在里间的小床上休息:“你睡半小时,我在外面写笔记,醒了我送你回中药房。”丁秋楠怀孕三个多月了,虽然反应不严重,但还是容易累,中午能睡一会儿,下午才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