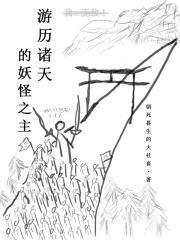91言情>离宫後,陛下表弟後悔了 > 不是她(第2页)
不是她(第2页)
德元茫然地啊了一声,脖子僵硬地往上一擡,见天子伸入盥盆净手,漠然道,“她不是董娇,让白岩速速来见朕。”
河里淹死的不是娘娘…
可那具女尸上穿的戴的,样样都是娘娘的衣物,陛下既然如此斩钉截铁,想来不会有错。
还好,还好不是娘娘,不然准没他好果子吃!如今只要人还活着,他就有亡羊补牢的机会。
诶…陛下素来爱重娘娘,这次居然直呼大名,可见是娘娘使计将他们都蒙骗了去,才惹得陛下如此气恼。
德元眼睛圆溜溜转了八百回,回过神当即道,“陛下火眼金睛!奴才愚昧,奴才这就去召白大人。”
天子背手,伫立如松,眸光森寒刺骨。
昨夜董娇出逃,竟无一人发现,定是下了迷药,此事她一人做不到,背後定有他人襄助。
山脚有龙骑卫把守,董娇为了绕过他们,游到另一座山,且大周各道水路鱼龙混杂,她应是一直走的水路。
天子薄唇微扯,好巧不巧,白岩正是他在萍遥亲自拿下的水匪头子。
诸侯各国的水寇虽多,但大多群龙无首,难成气候,所做之事多是抢劫而非害命,和匈奴骑兵相比,威胁不值一提,他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治这些水寇,堵不如疏,索性就亲自扶持二三位,反倒能成为一条出其不意的暗线。
三日後。
白岩恭声道,“禀陛下,卑职幸不辱使,已在广川一带找到娘娘的踪迹。”
天子端坐高堂,手中捏着条陈,不紧不慢问,“在广川何处?”
白岩将地名道出,紧接着补充道,“照着娘娘的路线,似是要一路北上,直达冀州,卑职在冀州的手下也发现了一艘货船,船上的人皆是练家子,行事风格跟娘娘的护卫如出一辙。”
言及此处,白岩止住,眉头拧成一团,天子见他面色挣扎,放下条陈,凤眸微眯,“还有何事?让你如此为难,不敢说。”
“此丶此外,卑职还在那艘船上查丶查到一位男人带着幼子,卑职的手下怕打草惊蛇,不敢靠太近,只听见随从们唤姚公子和小主子…”
天子面色冷峻,另一手的御笔顷刻被捏断,一字一句道,“你是说,董娇不光骗朕死了,还背着朕偷人,连孩子都有了?”
白岩本是个混不吝的水寇头子,乍然得知自己比天还大的主子居然被董娘娘明晃晃地戴了顶绿帽,着实想咧嘴发笑。
可他爱惜自己这颗俊朗的头,为免牢狱之灾丶笞仗之苦,只好极力将嘴角往下撇。
“没想到她还藏了其他的护卫,难怪还有闲情跟朕玩回心转意的把戏。”
天子凤眸一转,杀意如暴雨倾盆,拍桌道,“继续给朕查!把太皇太後给她留下的部下,都给朕拎出来,看日後谁还能救她出去。”
董馥娇已至广川地界的渝东县,再过两日就能抵达冀州。
可她在船上晕的实在厉害,便下船,扮男装到镇上寻了最宽敞的书馆歇息一二。
书馆里三三两两坐了人,有几位不像是来看书丶买书的,倒像是说书的,碎嘴道,“诶,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县太爷的二姑娘被广川王看上了,还没等宣召纳入宫,直接寻了根梁往上一吊,香消玉殒了。”
“可不是嘛,那哪是广川王,那是活阎王!谁骨头这麽硬,敢去伺候他,没过两日,别说是一整条命了,鼻子丶眼睛都给你挖空咯!”
“还得给你挫骨扬灰!烧的干干净净!一块好肉都不给你留!”
董馥娇拿话本的手一顿,诧异地扬眉,「玄茂,他怎麽变得如此暴虐,果真如此吗?」
她入主中宫以後,就再也没见过玄茂,印象里他虽沉迷女色,可也算是老实敦厚,绝做不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好端端的妙龄少女被他这样糟蹋,如若这些都是真的,那他还是人吗?
董馥娇忽而觉得,跟玄茂一比玄彻也不算丧心病狂。
他再正常不过了!皇祖母也称赞他是天生的帝王。只不过她受够了做皇後的委屈,才对他有生了成见跟嫌隙。
如若不是玄彻非要她回宫,如若她只是个在长安城逍遥享乐的郡主,还不得殷勤抱住这个陛下表弟金闪闪的大腿。
大腿。。。董馥娇斜眼一瞟,不经意地透过书架的空隙,见一道欣长挺拔的侧影,银冠束发,身着钟乳灰暗金蟒袍,闲庭信步踏入书馆,步步冷冽。
董馥娇难以置信张开唇,这通身清贵,不怒而威的气场,不是玄彻还能是谁。
他怎麽在这?
董馥娇心惊肉跳,闭眼赶忙平复心绪,旋即不动声色地将话本搁下,转身走出书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快步行至岸边,时至酉时,渡口上渔船星罗棋布,橹声欸乃连绵不绝。
董馥娇左顾右看,只在几息间就找到了风息的那艘船,她猫着身子上船,却见船内空无一人。
身後传来玄彻凉飕飕的声音,“阿娇可是在找你的护卫们?”
董馥娇咬紧腮肉,心道糟了,风息他们肯定早就被玄彻擒住,若不是她一时兴起,非要下船,想必早就碰上玄彻了。
哎呀!董馥娇站在船舱内,心里茫茫,不知东南西北,只知一点——她不会撑船呐!
更要紧的是,她往外一探,船只太密,接踵而至地相连,根本水泄不通,即便是跳河都得捂着脑,怕磕到哪艘船,水还没下,人先撞晕了。
董馥娇神色郁郁,听见沉稳的踏步声後,杏眸里的秋水更是凝成冰花。
玄彻上船了。
这次她又要束手待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