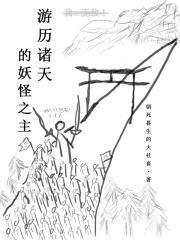91言情>穿成反派嫡女,掌掴绿茶 > 第9章 她想让我跪那我就掀了这棋盘(第1页)
第9章 她想让我跪那我就掀了这棋盘(第1页)
禁足令解除那日,春桃把包袱捆得死紧,我却站在冷院破门槛前没动。
风卷着炭灰往脸上扑,我盯着廊下那两个空炭盆——王氏撤炭时,大概以为我会像原主那样哭哭啼啼求她开恩。
可她不知道,这冷院每一片碎瓷、每一团湿棉絮,都是我给她备的棺材板。
小姐?春桃踮脚替我拂去肩头炭灰,回正院的马车在门外候着呢。
我摸了摸袖中那张字据——昨日沈福带着账房先生来清点,我让春桃把炭盆缺口、药罐底的霉斑、被褥里的水痕全记在册。
墨迹还未干透,纸角沾着点冷院的泥,倒像块烧红的烙铁。
不搬。我弯腰捡起块炭渣,在斑驳的院墙上画了道竖线——这是我在冷院的第二十七天。去把炭灰收进木匣,再找账房要十盆新炭。
春桃眼睛一亮:小姐是要
要让全相府的人都看见。我望着她顶翘起的呆毛,看见沈清棠被禁足时,住的是漏风的屋子,盖的是霉的被,喝的是凉透的药。
她抿着嘴笑,转身跑向偏房时,裙角带起一阵风,把墙上的炭线吹歪了半寸。
我望着那道歪线,指尖轻轻抚过——歪就歪吧,等王氏的体面碎成渣,再让她给我描得端端正正。
消息传得比春桃的脚步还快。
次日午后,我在冷院晒炭灰,听见几个粗使丫鬟在院外嚼舌根:听说嫡小姐把冷院的破东西全记册子了?嘘,夫人昨儿摔了三个茶盏,茶盏碴子扎得手直冒血呢。
我捏着炭灰的手顿了顿。
王氏惯会装贤良,从前原主被苛待,她总说为了磨磨脾气,如今我偏要把这摊在太阳底下晒——让族老们看看,让父亲想想,让全大宁朝的人都知道,沈相府的嫡女,是怎么被继母磋磨的。
三日后的小宴,王氏果然上套。
我站在镜前,春桃举着件洗得白的湖蓝衫子直撇嘴:夫人让人送来的,说是旧衣更显规矩
我摸着母亲留下的白玉兰簪,冰凉的玉贴着耳垂。
那是母亲咽气前塞给我的,当时她咳得说不出话,只把簪子往我手心按了又按。
我望着镜中自己,素白裙裾垂到脚面,间那支玉兰没有珠翠衬着,倒比满屋子的锦绣更干净。
就穿这个。我对着镜子理了理裙褶,规矩?
我倒要看看,谁更懂沈家的规矩。
前厅里,王氏穿了件金丝绣牡丹的褙子,鬓边插着东珠步摇,走动时叮铃作响。
她见我进来,眼尾挑了挑:清棠,你这素色
母亲。我打断她,女儿记得,父亲说过嫡女衣饰当雅,不可逾制
她的笑容僵在脸上。
族中三老太太正扶着丫鬟往主位走,瞥见我间的玉兰簪,忽然顿住脚:这簪子像极了当年沈夫人的。
沈相正在给族老奉茶,手猛地一抖,茶盏磕在案几上,溅湿了半幅衣袖。
他抬头看我,眼眶慢慢红了——当年母亲病中,总爱戴着这支簪子坐在廊下,说玉兰香能压咳。
席间,沈清瑶夹了块桂花糕推到我面前,指尖上的珊瑚护甲闪得人眼疼:姐姐在冷院可还习惯?
昨儿听门房说,夜里冷得连老鼠都冻死了。
我捏着银匙的手紧了紧。
她说话时,王氏正用帕子掩着嘴笑,茶盏沿儿在她唇上压出道红印。
老鼠死了,蛇却活得好好的。我放下银匙,望着沈清瑶间那支和王氏同款的珍珠簪,躲在暖窝里,吐着信子等人心软。
满座静得能听见炭盆里的火星噼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