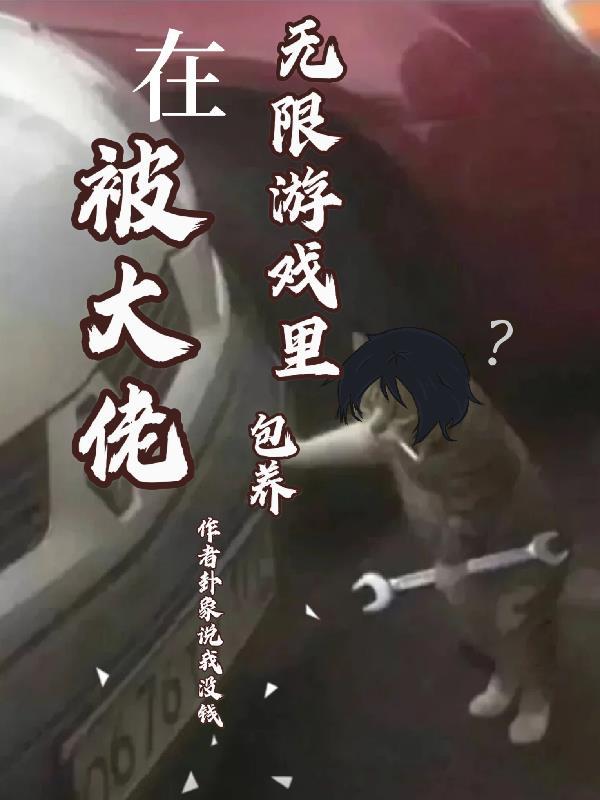91言情>少女前线:141指挥官 > 第1228章 警戒高度(第1页)
第1228章 警戒高度(第1页)
“我相信二十米的高度……”陈树生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像夜风把子弹壳吹过钢梁,轻得几乎要被头顶那盏漏油的日光灯管嗡嗡声吞掉。
二十米,相当于七层楼,相当于一枚炮弹从射到坠地的完整抛物线,相当于缓冲气囊在零点三秒内被重力撕成碎布的死亡倒计时。
陈树生说这话时,拇指正无意识地摩挲着战术手套边缘磨出的毛边,那动作慢得像在数战友的肋骨——每根肋骨下都藏着一条可能断掉的命。
“所以我不希望有人变成废铁,明白吗?”他停顿了半秒,喉结上下滚动,像是把后半截话咽回去又吐出来。
废铁,不是比喻,是陈述。
他见过太多被炸成零件的战术靴,见过钢盔里黏着半张工牌的照片,见过缓冲芯片烧焦后冒出的蓝烟在雨里凝成一朵毒蘑菇。
当血珠渗进尼龙纤维的样子像给布料绣了条暗红色的警戒线。
如果二十米的高度变成现实,这道划痕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从膝盖里戳出来的骨茬?
会变成急救包纱布上永远洗不掉的锈斑?
“当然如果能利用这一点做陷阱最好。”他说这句话时,嘴角肌肉抽搐了一下,像被回忆抽了一耳光。
“但执行作战任务不代表可以把自身完全当筹码。”他的声音突然沉下去,沉到战术靴底的钢板都能共振。
日光灯管闪烁的频率和他心跳同步,每一次明灭都在提醒:这里不是游戏,是真实世界。
“这不是我第一次强调,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嗓音突然变得异常严肃,像一把出鞘的军刀抵在喉间,刀刃上倒映着所有人的脸——那些脸在防毒面具镜片里扭曲成变形的月亮,像随时会碎。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腰间的手枪套,金属扣件出清脆的“咔嗒”声,像是给这句话打了个冷冰冰的句号。
所以他必须强调,像强迫症病人反复确认门锁。
因为陈树生比谁都清楚,战场上的“疏忽”不是笔误,是墓碑。
他身体微微前倾,战术背心的尼龙带子出紧绷的咯吱声。
“毕竟你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有着相当长的时间会活动在高处。”他的目光扫过scar-h的机械关节,仿佛能透过装甲看到里面的精密部件。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金属扭曲的呻吟声,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陈树生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节奏如同倒计时。
我可不希望我的队友体验从二十米高自由落体砸到钢筋或者机器上的感觉。”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一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投影仪的光线在他脸上投下锐利的阴影,让那道伤疤显得格外狰狞。
“即便你们是人形,有着皮下装甲还有缓冲层的保护……”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这个事实在空气中凝结。
会议室里的通风系统突然停止了运转,死寂中只能听见电子设备出的微弱嗡鸣。
“但这个高度足够让你们失能了,明白吗?”他的指尖重重敲在桌面上,出一声闷响,像是给这句话盖上了血红的印章。
scar-h的散热风扇突然加运转,在密闭空间里出细微的蜂鸣。
陈树生注意到了这个反应,眼神变得更加锐利。
“我也在这里强调一下,”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几分,像是雷霆前的闪电,“我们确实以完成目标为第一要务——”战术靴在地板上碾出一个尖锐的转向声,“但我绝对无法接受我的队员因为一些细节上的疏忽而白白丧命。”
他的拳头突然砸在战术地图上,震得对讲机都跳了起来。
“这一点我是无法接受的。”
“二十米的高度吗?”scar-h的瞳孔微微收缩,光学镜片自动调节着焦距,仿佛在模拟那个令人眩晕的高度。
窗外,暮色正在吞噬最后一缕阳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雪。
考虑到马上就是晚上了,甚至可能还有风雪天气,如果真的活动在厂区的屋顶上,确实无法分辨采光板跟其他屋顶的区别。